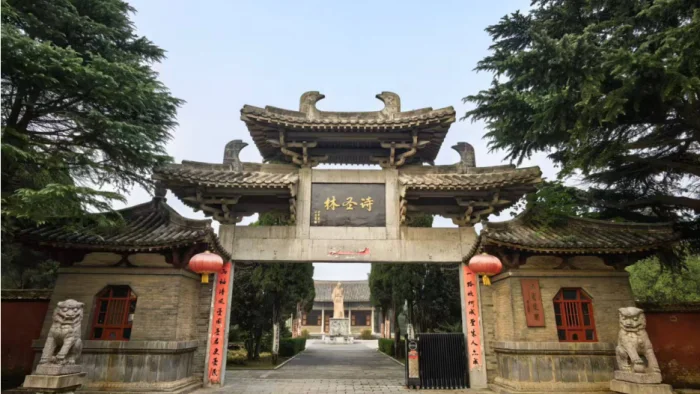引子
范强写我了,我就不好再去范强的文字面前饶舌了,这本书里无论是描述哪个人物,无论有无调侃,都是要把“表扬与自我表扬”进行到底的!只能讲一句话,我做很多事情都是会去找范强的,这样会给自己添点底气。

写范强的是我的弟弟。
齐岸民最初在这本书里是要作为受访者出现的,我坚持了一下,要他放在其他地方表现。以往,家人和朋友在总结齐岸民的成长路程时,往往会指出我对他的奇怪的严苛和障碍。尽管如此,还是没有阻挡了他在文字写作、艺术创意圈子里的影响力。前些年朋友们就说过,以前介绍他时会说:这是齐岸青的弟弟。现在要介绍我时会说:这是齐岸民的哥哥。

我们的父亲去世早,我在家里老是端正站立着。家里多一个愿意恭敬文化的,其实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范强也是我的兄弟!
——齐岸青

范强 石战杰 摄影
范强是阅读者,同时也是阅读制造者。这样的结论,基于过往和现在的范强,所能构成的个人阅读史和书写成果。
从范强的书屋里,我看到一个持续阅读者无法掩饰的外化物象,那是自己熟悉又亲和的场景。这种场景源自书籍营造出的气氛,甚或连带着气味,只有图书馆、书店存在这种被拉满、被羡慕、被赞誉的空间围合。
范强家不单专设了书房,连客厅、卧室甚至储藏间都预留一隅以纳不断增量的书籍。范强先生私域不独书籍,绘画、雕塑、图像以及文杂间或其中。如是不事外宣的日常家庭细碎、局部,无疑隐性地透露出主人的习性、嗜好、品位、追求等。想想一万五千册书籍的所有权者,倘如不为阅读,要这么多书做什么?只有专司收藏书籍者例外,范强显然非收纳偏好者。
其实,最早知道范强先生,是因了他的摄影集《九场所》《精彩郑州》。他街拍的习惯已延续二十余年,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依然是我们眼熟并忽略的郑州城市街景。范强以及同时代所有街拍者,都是不经委托亦复兴趣使然的摄影者,这种记录式的拍摄,随着岁月延伸所形成的“蹉跎”感,会莫名地唤起阅读者隽永的记忆。就地域图像而言,无论魏德忠的《老郑州》《红旗渠》、姜健的《场景》《主人》《筑城者》还是范强的《公共空间》《九场所》,俨然成为我们阅读过往、记忆过往的“图像档案”。
范强所构建的城市图像,可以视同对于一座城市的阅读,它不是城市风景,不是具体人物,不是新闻事件的“攫取”,而是客观地将人与公共空间置于一种关联,辅助主观“剪裁”并凝固于图像介质中,继而形成接受性阅读。范强的摄影本质,存在着自我阅读与被别人阅读的视觉连环,他主观强烈地预设了这种存在。
阅读的概念,并不限于古老的刻写版、竹简、纸页和屏幕的传递,连接人体最敏锐部位眼睛所收纳的自然景物、人文图景、世事流变都可以视为阅读,换句话说,阅读有狭义与广义两说、两维。
至于范强阅读的维度是自有能动还是主观后觉,推测极有可能是并行推演的结果。事实上,获取阅读多维能力者,必然内存“阅读思维”,其与单纯的阅读有着质的区别,一如艺术家与画家、雕塑家、版画家的区隔,前者以哲学统领行使艺术实践,后者以主观志趣借助技术塑形、涂抹、刻画乃至造美。
大凡具有阅读思维者,双眼之外另有第三只眼看世界,有将日常琐事处理清爽、快速调频的能力,比如无论多么繁忙仍可以自洽到一种逻辑状态。范强没有给自己预留困顿、迷茫、别扭的余域,没有让自己的新书招尘、笔墨干涸,而是竭尽余暇地以微观历史的视角、非虚构文学的手法,敏锐地捕捉郑州城关键时期、关键节点、关键事件并基于文献、采录,兼之主观辨识、梳理、归纳融合笔记、地志、历史的书写体例,陆续书写了《双塔记》《郑州人》《水龙吟》《新省会》专著,意在迫近还原一个时期、一个侧面、一个微观的郑州史,他凿通了制造阅读的时空隧道,还原了一个比一般人卓尔的自己。
如是卓尔的范强(其个人未必这样认定),必然有一个前范强潜力的存在,尤其自后推前复述一个人的阅读史,最想知道初始阅读的故事。果然有一桩往事抖搂: “我小时候就住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家属院里,离医院不远”,这不远的距离促成了他和同院的小伙伴经常“嬉戏的场所”,因此“对医院的每处设施,都再熟悉不过了”,可以完全处于“东奔西跑,无拘无束,如入无人之境”的撒欢状态。撒欢之间意外地发现被封存的书库,于是范强参与了将书悄悄地装袋、拎家的秘密行动,风高夜黑中移出库房的书多是少年看不懂的医学典籍,仅有《小经洞》《董存瑞》《老残游记》三本书尚属人文读物,其中《董存瑞》最迎合那个时代少儿认知热点,也最令少年范强如获至宝、倾心阅读,由此圈存了其个人记忆并成为个人阅读演进史的叙事起点。
我倒不认为少年范强一次“拿来主义”的阅读经历,会就此奠基其未来的阅读、书写之路。唐诺先生讲:“阅读之难,不在于开始,而在于持续。”我深以为然。直至今天范强依然保持夜读一本书并随手标记的习惯,无疑此习惯乃后天经年累月养成,包括书写的习惯亦然。
此外,范强的阅读、书写系内循环并合式的,其自认基于个人的“三有观”,即有心、有情、有趣。范强将其视为人生“三友”,并以此赋号一间书房谓“三友居”。随着存书的递增,与之对应,书房的间数不得不扩量,于是雅号也就多了起来——东风草堂、厚乐堂、东张西望斋、聚忆堂、鄙庐等。雅号纯属遂心、遂意、遂念,那“东风草堂”不过是因家宅临东风渠边而得名, “鄙庐”则系此书房位于城郊的缘故,至于“东张西望斋”无非是时常从郑州西区回父母家陪护而特设书房的冠名。若深一层解析,则意指杜甫草堂、子产北鄙、东西文化研究的隐喻。至于新近的“聚忆厅”,灵感来自《水浒传》梁山好汉“聚义厅”的谐音梗,一字替换的另层意思则表明其收集、记录、整理、书写关于郑州历史的集体记忆和私人记忆的旨趣。至于雅号,乃古代文人雅趣,传习今天依然是雅趣。
论阅读、论书写,最紧要的是舍得花时间,多数人的时间看似很从容、自由,其实不然。时间都跑哪里去了?很多人会重复、循环以至于无趣单调地进入管道生活模式,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间或在路上、在等电梯,每天的时间轨道几乎是被规定好的一样,或被一种自我懒惰、拖沓、平躺白白消耗了。
范强将自己从时间管道里拔了出来,依据自我判定的价值顺序调度时间、利用时间。就其个人工作履历看,无论任职城建、交通或旅游机构管理者,多善于以工作为基准点,自行学术性研究、调研、实践,此处自有相对应的实绩可圈可点,而闲暇之余文学性散文、随笔则是其书写的“号外”专著,《城市伫望》《街巷散步》《居留与游走》《私人记忆:非虚构微故事》等,范强的一部分时间毫无疑问都跑到写作上了。时间不独是时间,它会自带、附着情绪。如不尽兴、不愉悦,一个人的阅读和书写就无法持续,阅读是相对隐性的私密愉悦,而书写往往自带复刻、转印的公开意念。
范强的阅读基础,不囿于白纸黑字、数字屏字乃至于语音、视频,无字冥想地阅读过去、阅读现在、阅读未来,也可以视为阅读的一种,此乃你我无法观看到的范强内部,而实存于生活中的范强,和我们中的大多数无故不离身的手机,和我们中的少数置于书桌电脑前以码字为能事者同频、同道。
问过范强的阅读习惯或阅读技术,非如宋儒朱熹《读书之要》中的“大抵读书,须先熟读”要义,范强阅读规律略有改易:先泛读,再熟读。泛读是寻师,熟读是拜师,而二者阅读终极目标则是借助他者的书写,犹如“出于吾之口”,犹如“出于吾之心”,这种他者与我者的转化,范强抓到了“点位”,毕竟在范强看来若实现古人“读万卷书”的标格,并非一字不漏地过目阅读,泛读是必然的,熟读是必须的。
至于“行万里路”,范强认为在不费脚力可行万里的当代,所谓的公里数已经不重要,孔子、嬴政、法显、张骞、玄奘、徐霞客等古代行者路程,当代人多能够超越。范强说他去过三百座城了,每座城都是一本书,倘若不将游历设定为一种体验式阅读,去过的地方再多亦是观光。
有如是新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八字者,大概逼近属于新的理想状态者,他们或可称谓新时代“八字”标格者。
联想拎着相机游走、伏案阅读、归宅码字并将书籍视为工具的范强,他的身份已经被认定为城市文化学者、城市历史的书写者,而我在想,是什么力量日久天长、不期然而然地塑造了他个人的专长,是阅读与书写的并合能量,促成了过去、现在范强的本质,或是人生某处节点触发了他、点燃了他?那本少年读物《董存瑞》不至于那么重要吧,最多属于过往阅读故事一则。
生成实际真实的范强本质,是否为阅读与书写并行流变的结果,常规思维可以这般认定,然而另种无形的力量或独属于他个人的力量生成,可能存在却又说不清楚。能够说清楚的是:许多识字者并不经常读书,经常读书者未必能够成为书写者;此外,与其说书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技能,不如说是一种志趣的自然养成。我和范强先生大致认可这等说辞吧?
最后,补充一点跑题的话:曾经以为自己的存书足以“砸人”了,过眼范强先生家宅存书之丰富和芜杂后,再度领教了什么叫——山外有山般的类差。
范强
笔名婴父,1960年生于郑州。文化学者。曾任郑州市旅游局局长、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郑东新区党委副书记等职。出版文化专著十余部。
(《郑州阅读》由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统筹:梁冰
编辑:张晓璐

本文(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音乐、视频等)版权归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需转载本文,请后台联系取得授权,并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同时注明来源正观新闻及原作者,并不得将本文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