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许很难用作家去定义张宇,但他又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他很会“玩”,盆景、足球等玩得投入,还玩出了名堂。青年时当过洛阳地区文联主席、洛宁县委副书记,对人际关系有着一肚子的心得。
张宇又是一个会“逃跑”的作家。他心念文学,离开官场后,潜心写小说。中年时又从文学圈跑到了陌生的地产圈,担任建业集团副总裁,后又“误打误撞”闯进了足球圈,还担任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宇的经历似乎和作家的身份不沾边,可他实则太想体验生活了。如他所言,作家是黑夜里的动物,当他“吃透”了这个行业,关起门来又写起了小说。

著名作家张宇 周甬 摄
20世纪80年代,张宇因创作中篇小说《活鬼》而享誉全国,从此被誉为文坛“活鬼”。“作为作家,应该写出经得起历史和时代考验的作品。”作为曾经的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莽原》杂志主编,张宇不仅将这样的标准贯穿于整个文学创作生涯,同时也将这样的思想带到了文坛。正如张宇自己所说,文学离不开生活,他的长篇小说《晒太阳》《疼痛与抚摸》《软弱》《检察长》《足球门》《呼吸》等,都是他长期思想的结晶,也是他在文学艺术之路上的探索。
如今年过七旬,张宇仍笔耕不辍。他说要做些愿意做的事情,想说些愿意说的话。盛夏时节的一个下午,在张宇的书房里,正观新闻记者与他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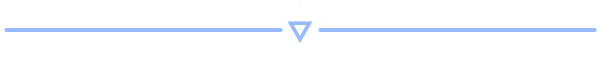
谈文学创作
正观新闻记者:文学的种子最早在您心里是什么时候播下的?您的处女作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张宇:这与一位特殊的老师有关,他叫吴兴民,河南大学地理系毕业,他出版过诗集,才华横溢,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学生们都愿意听他讲课。
他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那是在1970年之前,我还是高中生,当他第一次给我讲普希金、拜伦的时候,我的大脑就晕了。他问我,“当你在月下,一位姑娘举着一杯红酒,邀你共饮时,你在想什么?”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听到这句话,我很震惊。老师说,这来自文学,从那时候起,点燃了我的文学火种,我开始写诗。在他督导下,我阅读外国文学,是他影响了我的一生。
时间来到1979年,那时我从工人转到洛宁县广播站当一个小编辑,下乡采访时,我发现了农民做梦都想要拥有自己的土地,于是我写了处女作《土地的主人》,在《长江文艺》头题发表,当时《红旗》杂志给予的评价是“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了农民对土地愿望的第一篇小说”。那次拿了66块钱的稿费,比一名高级干部一月的工资还多,在县里很轰动,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写小说了。
在《土地的主人》发表之前,我写过一二十篇作品,自学成才的业余作家没人辅导,只能逼着自己一直写。后来一位编辑告诉我,那些作品大部分可以发表。我也不觉得吃亏,自己得到了磨炼。

正观新闻记者:您的作品大都是现实题材 ,注重探寻人物的精神世界,您如何理解创作和现实的关系?
张宇:生活就像发面的酵母,文学不是从现实搬进来的,而是“发”出来的,从而无限深化。我曾开文学评论家鲁枢元的玩笑说,他是用一颗大米就能做成一锅饭的人。
我的长篇小说《呼吸》后记,标题就叫“虚构的空间”,说的是一个作家的才华就是虚构,要有虚构的能力。虚构的空间,这才是小说家的乐园。
创作与生活紧密相关,二者不是脱离的,创作得以生活为根。所以我认为生活跟创作的关系,生活永远是根,创作是情感赋予“根茎”生长和开花结果。
正观新闻:您又是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并融入生命体验的?
张宇:我是从日常生活中积累灵感的。人活着,要接触人,到处都是生活。能否从中发现美,能否从点滴生活出发去想到整个历史背景下社会发生的转移,这是一个作家的才华。
例如,我的长篇小说《软弱》,写的就是两个警察的故事。我跟着一个民警7天体验他的工作生活,他讲了很多故事,但我没用,这是我的写作习惯,我不采访具体事件,我喜欢从生活中感受生活,进行升华。

正观新闻记者:翻阅您的作品,求新求变可谓是“主旋律”,诙谐幽默,跌宕起伏,耐人寻味。作为小说家,在语言、故事、结构、立意上,您有怎样的追求或体会?
张宇:每一个题材、每一个人物,它都有一种独特的语言等待寻找。我一般会去找几种适合作品的叙述语言,我写过十多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甚至都不像是一个人写的。
小说的结构是小说家的本事,写作每一部书时为了结构往往绞尽脑汁。
在立意上,我并不喜欢针砭时弊。我个人认为我不是一个“近视”的作家,对当下社会没有哪个人是永远满意的,小说更重要的是见识和认识。
正观新闻记者:从《活鬼》《疼痛与抚摸》到《对不起南极》《呼吸》,您从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仍笔耕不辍。您怎么看待您的文学生涯?
张宇:“浪得虚名在,其实糠包菜。没有真学问,混个穷自在。”我曾作打油诗比喻我的文学一生。
人一生认真地做好一件事情就很好了,高境界不是做得好与不好,而是一直做。我觉得文学也是如此,我喜欢文学,我摆弄了文学一辈子就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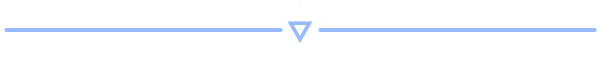
谈职场经历
正观新闻记者:我们了解到,您高中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工人,做过洛阳地区文联主席、洛宁县委副书记,可谓前途光明,但都突然不干了。您的思想在此前后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宇:1984年,国家要提拔年轻干部,恰好那年我32岁,在洛阳的青年作家中就数我最出名了,在全国也有名气。于是时任洛阳地委书记的杨光喜同志,看过我的小说,经过组织推荐和考察程序,选我做了洛阳地区文联主席。
后来省里有一个作家体验生活的指示,省委组织部第一批选了4个人兼职锻炼,我被派到了洛宁县去当第一副书记。
在县里工作了两年,可我还是想当作家,我和杨书记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我前程大好,为何还要离开。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官,我回来后继续当作家,天天骑个破自行车,反而非常舒服。
正观新闻记者:您曾担任多年的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您如何看待“文学豫军”现象?
张宇:河南作家沾了语言的光,河南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全国人都看得懂。河南毕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文化底蕴深厚。此外,咱们河南老一代作家对青年作家传帮带的感情特别深厚,看到后辈作家有才华,特别激动,看到他们有缺点,特别心焦,就忍不住提出建议。

正观新闻记者:您还担任过多年的《莽原》主编,您认为,编者与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宇:我做了7年《莽原》主编,一期发稿约40万字,每期我都要看。当主编要想到,很多年轻作者从这里出发,要成长,这个位置就是要培养作家。
我对编辑的要求是,可以删,不准添,要保留作家的风格。此外,一个编辑要有眼光,如果作品一时达不到发表的水平,要给作者写回信,或是打个电话鼓励他。除此之外,一个编辑还要有责任感,敢于发表作品,并承担责任。
正观新闻记者:当迈过70岁的门槛,对您来说体悟最深的是什么?目前您投入精力较多或思考较多的事情是什么?回顾您几十年的创作等经历,可否对自己做一些阶段性的总结或评价?有哪些满意或者遗憾?
张宇: 70岁后我最深的体会是“不怕了”。一是不畏惧死亡,我年轻时体弱,本打算活到60岁,一不小心活了72岁,这样看来,我是赚的。二是不怕外界的干扰和诱惑了,来日不多,我要做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想对读者说一些亲切的话。
回看往昔,我本是一名工人,能找份工作就已是心满意足,结果当了个作家,又一不小心当了省作协主席,我已经很满足了。但多年来,我也有遗憾,没有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做出过更加突出的贡献,为此耿耿于怀。
于是,我还想再写一部长篇小说,前年写完了《呼吸》,这或许是我最后一部作品了,作为对这个社会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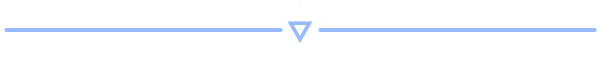
谈生活体会
正观新闻记者:您平时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有什么兴趣爱好?
张宇:我的时间安排很简单,早上精神状态好,我开始写作到11点,下午就看书、聊天、喝茶、摆弄盆景,有时候搓一盘麻将。
有人请我吃饭喝酒,我很少去,有些人说我不识抬举,其实大家不太了解我。我特别喜欢独处,喜欢一个人发呆,没事时,四处游逛,是一个懒人,这是我最享受的状态。
阎连科说我“不务正业、玩物丧志”,他忘了,其实这就是张宇。我把自己称为城市里的“二流子”,到了如今这个年龄,一定让自己闲下来,特别是心境的悠闲。
正观新闻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阅读的?在阅读中,您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
张宇:年轻时我就喜欢乱翻书。我有句“名言”,只有阅读,你才能和大师对话,和高人对话,和各个民族优秀的人才对话。因为他们在作品里都是真实的,从不隐瞒自己,就看你会看不会看了。
读书时,要多加思考,站在作家的那个时代高度,看他讲述些什么,启发你在这个时代写些什么。一个作家是从阅读走过来的,可以说,没有阅读就没有作家。
正观新闻记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您对年轻人有哪些建议吗?
张宇:当下网络上的一些内容如同垃圾,受众也不进行思考,把大脑都填满了“废料”。作家是黑暗中的动物,独自在角落写东西的人。这些年,我从来不上网,也不使用微信,但并没有落后。
正观新闻记者:您曾说过,作家的眼光应该不同于普通人,是独立的、个性的,能谈下您的理解吗?
张宇:我对这个时代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这个时代走在高科技快速发展的路上,同时也在走向灭亡。人类为了利益,不抑制自己的私欲,对自然破坏,对环境破坏,这是反科学的、反人性的,是走向毁灭的开始,值得警惕。

统筹:石闯 李记波
编辑:高畅韵

本文(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音乐、视频等)版权归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需转载本文,请后台联系取得授权,并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同时注明来源正观新闻及原作者,并不得将本文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