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承号会客厅70期嘉宾:

王克明,陕北老知青,辛亥元老任芝铭后人、任均次子。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历史继承性的研究。
11月18日,辛亥元老任芝铭后人王克明向郭仲隗纪念馆捐赠珍贵史料《任芝铭存稿》,郭仲隗后人郭力教授代为接收。

任芝铭先生,任锐和任均姐妹的父亲,孙炳文和冯友兰的岳父,孙维世和宗璞的外祖父,前清举人、同盟会会员、士绅地主,北伐从军、抗战入伍曾遭清廷通缉、袁党追捕、韩复渠下令枪毙、汤恩伯关押,后任新中国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1938年冬,任芝铭送女儿任均到延安,见到mzd时,曾讨要游击战术文字,因“尚未编出”,未能如愿。返乡后从事新学教育,任县中学董事长。此后,先后就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高级参议、新蔡县参议会议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纵观其一生,可谓亦文亦武,能上能下,为学为政,不求不居。

1977年秋,冯友兰夫人病故,留下一个纸包。里面是她保存的父亲遗物,有证书、家书、委任状等。其中的家书厚厚一卷,是其母亲当年仔细粘贴、缝订成卷的。那是任芝铭“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记录,更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物证。这份遗物逃过了“wg”浩劫,传到任均手上。三十年后,任均交给儿子王克明。
2010年,王克明打开纸包,细读任芝铭书信诗文、工笔小楷、斯文华章,感觉“民国扑面而来”,越读越觉得放不下,遂用心查证注疏,整理出《任芝铭存稿》一书,还原了难得一见的民国早期知识分子家国文本。
2013年5月,由王克明整理注释、谢石华提供资料并争取县政府资助出版的《任芝铭存稿》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深受学术界的好评。

任芝铭(中)郭仲隗(左一)
郭力教授说,原新乡市委书记、新乡市政协主席田纪震同志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江流天地外----郭仲隗、郭海长纪念文集》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家两代人中,父辈在清末民初鼎革时期是社会进步的先驱,下一代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志士者,并不鲜见。就我们河南来说,新蔡的任芝铭及其女儿任锐、任均,商城的林伯襄及其子林萃、侄林孟平,新野的罗蜚声及其子罗绳武,新安的王广庆及其侄王励刚,偃师的杨勉帝及其子杨章武,南阳的杨鹤汀及其子杨廷宝、杨廷宾等都是例证。新乡出了郭仲隗、郭海长这两代革命者,值得新乡人引以自豪。
郭仲隗和任芝铭同为老同盟会会员,辛亥元勋,一生交集颇多。
本期宏承号会客厅,王克明先生讲述的是他表姐孙维世的故事。

维世1930年代在开封
作为亲属,我想到,今年,表姐孙维世诞辰100周年了。我们从小管她叫“兰姐”,在这样一个应该纪念的时间里,觉得至少该有篇文字,说一说她。几十年来,孙维世的养女孙小兰多次跟我谈起她的妈妈孙维世,都失声痛哭。我母亲任均对孙维世的怀念,刻骨铭心,每每提起维世死难,都泪流不止。在亲属眼里,维世对亲情的爱,对艺术的爱,远胜其他。她的卓越艺术才华没能尽情施展,实在让人惋惜。

1930年代在开封铁塔下。右一任锐,右二任均,左一孙维世
1. 没能实现艺术理想
九年前,国家话剧院为纪念孙维世诞辰91周年,曾召开“继承维世精神、弘扬国话传统——孙维世艺术成就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唯有赤子心——孙维世诞辰91周年纪念文集》,确认了孙维世的艺术地位。文集关注孙维世的天赋、才华、艺术成就和贡献,不采用耸人听闻真假不明的叙述,通过游本昌、雷恪声、石维坚、杨宗镜、蓝天野等近20位老艺术家的回忆,讲述孙维世的真实往事,缅怀杰出的戏剧家。

这是一张1930年代的照片。左起任锐、孙维世、任均
在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中,孙维世的名字不能被忘记,她是1949年后与焦菊隐、黄佐临并称的中国三大戏剧导演之一,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前身剧院的创建者—总导演,是卓越的导演艺术家。她是中国艺术界的文革受难者之一。
1921年,孙维世出生在四川南溪县。她的父母孙炳文、任锐,都是辛亥志士,曾为推翻满清追求共和出生入死。维世出生时,父亲孙炳文正与好友朱德筹划去西欧留学。第二年他们在欧洲见到周恩来,加入了中共,认为找到了真理。维世6岁时,父亲在四·一二事变中遇难。那之后,她随母亲任锐过了多年动荡生活。她从小喜欢文艺,爱学表演。1935年,任锐把维世和我母亲送到上海学习演剧。她化名李琳,先后进入东方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剧团,开始登上话剧舞台,参加了《大雷雨》《醉生梦死》的话剧演出。之后进入影业,在电影《压岁钱》和《王先生奇侠传》中饰演角色,1937年她主演了电影《镀金的城》。

1930年代,维世与舒绣文(右)在上海
抗战爆发后,孙维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演出抗日话剧。随演剧队转移到武汉,此后转赴陕北延安。1938年,延安的戏剧艺术爱好者开始从事话剧活动。孙维世参加了抗战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在剧中饰演大小姐。当年,她又受邀参加了延安鲁艺抗战话剧《团圆》的演出。
1939年,她母亲任锐从延安调重庆工作时,她和我母亲一起去送别。然后约好维世周末再去鲁艺找我母亲相聚。但第二天,非常偶然地,她随周恩来、邓颖超去苏联了。在乌鲁木齐换飞机时,她给我母亲写信,告知她离开延安了。到苏联不久后,她考入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二战期间,她在苏联度过了艰苦岁月。

维世在苏联与瞿秋白同志的女儿瞿独伊(左)合影
以“大清洗”消灭肉体的方法巩固极权统治的苏联,那时没建立起消灭灵魂的目标,没有强化思想改造的目的,因此,虽然对文艺强调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但没有把艺术作为斗争的工具或武器来使用。孙维世就读的戏剧学院仍严格按照专业大纲进行教学。她极其珍视在最高戏剧学府学习的机会,大量阅读俄文版世界文学戏剧名著,钻研艺术理论,训练演艺技巧,甚至苦练舞蹈形体。那时,包括旧俄时代著名古典剧目在内,莫斯科的艺术演出非常活跃。她几乎观看了所有剧院上演的所有话剧、歌剧和芭蕾舞剧,并常参观画廊和博物馆。在去乡间体验生活时,她学会了许多俄罗斯民歌。

1940年初,孙维世在莫斯科与周恩来、任弼时等合影。前排左起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蔡畅。后排左起周恩来、陈琮英、张梅
在战时苏联,孙维世看到了阴暗的东西。但那时艺术没变成宣传工具,没有发生中国延安那种终结开放性的、对艺术和艺术工作者的大规模改造。所以孙维世能有机会集中精力,系统地完成表演系和导演系的全部专业课程,对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叶世界戏剧舞台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有了深入的学习、研究和实践。这个演剧体系虽然也讲思想和立场,但从动作到体验的方法,保持着对艺术的开放性探索。开放性是艺术的命门,是艺术家个人自由探索的空间。孙维世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面学习并研究斯氏现实主义演剧体系的戏剧专家。

1946年冬孙维世自苏联回国后从东北去延安,路过北平时在雍和宫前遇羊群留影
1946年孙维世回到延安后,进入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工作,1947年参加导演了歌剧《蓝花花》。之后被分配到黄河岸边山西柳林三交镇参加土改工作。调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后,1948年她导演了联大文工团的秧歌剧《一场虚惊》。文工团的工作是以文艺为工具、运用歌舞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

维世在1940年代

1940年代维世与马海德同志的夫人苏菲(左)合影
1949年后,孙维世曾有相对较好的条件从事艺术,而不是搞宣传。那时她追求热爱的人生事业,正是以人性和美为追求的艺术,而不是以政治蛊惑为目的的宣传。所以她会导演出因人物人性而引来争议或批评的《西望长安》、《同甘共苦》。后者因表现生活和命运的复杂性,曾被指为给革命干部脸上抹黑。
孙维世导演的话剧中,18世纪意大利哥尔多尼的《一仆二主》,19世纪俄国戏剧之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同时代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契科夫的《万尼亚舅舅》,和契诃夫的独幕喜剧《求婚》、《纪念日》、《明知故犯》、《
《钦差大臣》是1949年后中国上演的第一个外国古典剧目。孙维世的导演,显示了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驾驭经典巨作的才华与能力。《万尼亚舅舅》是她导演艺术的高峰之作。她准确地把握住了契诃夫笔下的人物,涓涓细流,丝丝入扣,高难度地演绎了人物内心的深刻冲突,表现了乡村自然生活中真实的幸福渴望,而不是革命性的为幸福而战。《小白兔》的成功导演,则使她成为中国儿童剧的奠基者。
孙维世导演的外国剧情话剧中,只有一部苏联的《保尔?柯察金》,是苏维埃革命内容的戏剧。这是她的第一部话剧导演艺术作品。她以多年在苏学习的积累,在排演中成熟地运用斯氏体系演剧方法,使话剧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提升了中国话剧的演出水准,并为建立正规的排演制度和完整的舞台艺术树立了榜样。这部作品使孙维世开始跻身中国著名导演之列。
孙维世没有参加过延安整风,没有经历过延安文艺的巨大变故,所以,她能保持着纯真自由的艺术个性。在1949年进城的中共文艺队伍里,经过系统性斯氏体系专业学习、全身心地投入艺术理想的导演专业人才,只有她一人。因此,只有她能成为那个时代斯式体系在中国话剧舞台的奠基人。那时,孙维世的艺术理想是,集合一批在艺术上有共同语言、共同追求的艺术家,创作不同风格的好作品,排演出一批世界名著,让它们成为保留剧目,长期轮演。她的剧目规划中既有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也有国外的优秀保留剧目,既有莎士比亚,也有赛金花。

1950年代在天安门。左起孙维世、任均、王一达。

1950年代在北京中山公园。左起王一达、任均、孙维世、金山
1954至1956年,孙维世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帮助苏联戏剧专家完成斯式演剧体系教学,培养了一批导演骨干力量。之后,她受文化部委托,挑选并集中训练班人才,组建新的示范性的国家话剧院。她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职务,改任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后来的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总导演。她参与创建了这两个剧院,为它们建立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多年以后,这两个剧院组成了中国国家话剧院。
为培养话剧人才,孙维世要求演员专心艺术、一丝不苟,对青年批评启发、悉心培养。她真诚透明,童趣活泼,正直豪放,笑声朗朗,为青年演员打开心灵的窗户,引导他们走上艺术道路。当年的青年演员石维坚回忆说:“没有孙维世,没有我今天。孙维世一个招呼说,跟我走,天涯海角不论什么地方,我都跟着走。只要有她在,我们愿意跟着走。”青年艺术剧院的老化妆师常大年曾回忆说:“孙维世可真是太好了,今后不会再有这么好的人了。”

孙维世与邓颖超、周总理的合影
但是,孙维世的艺术理想没能实现。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政治运动的实践,带来了对艺术的长期和严重干扰。她导演的反右话剧《百丑图》和歌颂中苏友谊的话剧《友与敌》,是她的艺术工作向宣传化政治转型的开端。从那时开始,她的艺术之路不得不越走越窄。1963年,她带领演员深入农村,与角色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排演了正面宣传歌颂农业合作化的话剧《汾水长流》。但是由于她没经历过延安整风,没搞过延安文艺,反而保持艺术理想地关注戏剧的艺术表现力,这个剧又被批评为歪曲丑化农民形象、不够革命化。孙维世的艺术追求,到那之后,实际上已经无奈地结束了。

金山和孙维世
孙维世导演的最后一部话剧,是她和金山编剧、大庆油田家属妇女业余演出的《初升的太阳》,在阶级斗争年代获得过好评。但那更应该被誉为艺术和艺术工作者都被改造后的成功的宣传作品,而非艺术作品。艺术生涯被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终结之后,孙维世离开了她集合起来的有共同语言、共同追求的艺术家们,再也没有可能实现她的艺术理想了。她的艺术才华被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摧毁了。
从艺术人生的角度说,孙维世生不逢时。文革乱世,她被卷进残酷的政治绞肉机,1968年10月14日被害死在狱中。一代卓越艺术家,成了文革受难者。今年10月14日,是她遇难53周年忌辰。
2.没有担任翻译组长
作为亲属,我们对孙维世没能全面发挥她的艺术才华,感到非常惋惜。戏剧界对孙维世导演艺术成就的认可,对她在现代话剧史中艺术地位的确立,使亲属们感到欣慰。同时,我们也愿意看到对孙维世的实事求是的叙述。在孙维世百年诞辰的时候,有的事情不妨澄清一下。
《中华读书报》2014年2月12日刊文,提及毛泽东1949年访苏时,写道:“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这一段描写是文学虚构,是对之前有关传言的采信和加工,而不是渲染描述真实事件。虚构是文学写作之方法,本无可厚非,但其中人物姓名不加以虚构,就容易使读者混淆虚实,以为事情真是那样的。
家人过去所知的是,孙维世在那之前去东欧参加活动,转到莫斯科等候任务,然后参加了毛访苏的翻译工作。但这还不是那次访苏亲历者的叙述。在周恩来警卫秘书何谦的访谈回忆中,和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师哲回忆录》一书中,亲历者讲述了那段经过。1949年,孙维世随团访问东欧,1950年1月回国路经莫斯科时,被师哲建议留下,帮助做了毛访苏后期一段时间的翻译工作。据此可知,前引文章段落是整体性的虚构。
第一,没有“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的情况。那之前,江青1949年去苏联看病四五个月,国内天安门举行政府成立大典后,10月6号她启程坐火车回国。她回来一个多月,毛泽东12月6号出发访苏。出发前,江青根据自己对苏联生活的了解,特别积极热心地就赠送斯大林礼品问题,提各种建议,包括大葱大白菜大白萝卜等。斯大林的外交活动,不喜欢夫人参加。师哲回忆说,一次几个苏联领导人跟毛泽东说想参观中国时,莫洛托夫建议请民主德国的格罗提渥总理也来参加。斯大林立即反驳说:“欧洲人是离不开老婆的,请他来就必须同时也请他的夫人,一个妇女参加到这个场合里来,谈话恐怕有些不方便。”
第二,没有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的情况。1949年7月22日,孙维世作为翻译,随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青年第二届代表大会和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又随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往东欧各国参观访问,共活动了五个多月。周恩来1949年7月19日写给邓颖超的信里说到孙维世:“二十二号她将出国。”所指就是这次。孙维世应在东欧活动结束后,1950年1月6日从莫斯科随团回国。周那时启程赴苏,能在满洲里相遇回国的青年代表团。1950年1月12日晚他在赴苏专列上写给邓颖超的信里说:“到满洲里不知能否遇到女儿,她回至北京

维世与邓颖超、周恩来在莫斯科合影
毛泽东1949年访苏时,随做翻译工作的是师哲。孙维世那时在东欧。在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所收毛泽东那次访苏期间的档案里,参加会谈的翻译只有师哲,没有孙维世的名字。毛在苏期间,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到莫斯科。师哲回忆说:“孙维世从欧洲参加戏剧表演活动回国,途经莫斯科,来看望周总理。孙维世是周总理的养女,我建议把孙维世留下来做些生活方面的翻译工作,周总理同意了。”这是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的细节。对比周恩来致邓颖超的信,在孙维世缘何半路参加毛访苏翻译工作这一细节上,何谦的记忆也是准确的。他们的记忆说明,孙维世是中途被师哲留下,而参加了毛访苏后半程的工作。
第三,没有“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的情况。因为孙维世那时在东欧,没有在那列火车上。周恩来也没有跟毛泽东同乘那趟火车,而是一个多月后出发去莫斯科。
第四,没有“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的情况。因为没有“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的前提,所以没有“滋味”。这样的文学描写,可以引导读者想象,觉得江青产生了像叶群那样的吃醋心理。文学性描写有益于讲故事,但因为涉及到我们的亲属孙维世的真实姓名,那么我就觉得应该说一说情况。江青对孙维世的态度与叶群不同。林彪曾在莫斯科追孙维世,但孙维世根本无心,只是保持着对著名抗日将军的敬重。孙维世的好友、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在苏联与维世同吃同住数年,她在回忆录《往事琐记》中,对这件事讲得很清楚。叶群后来知道林彪喜欢孙维世,便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吃醋心理。但江青对孙维世,不是叶群那种“大醋坛子”心态。孙维世多年领军戏剧舞台,名扬海内,有很高的导演艺术成就。而艺人出身的江青,有心独霸文艺天下,却一直无法抛头露脸,对维世的事业和成就,又羡慕又嫉妒。维世从苏联回来后,江青一直向她示好,几次邀请她去家里作客,但维世一直不卑不亢,没去过。六十年代,江青开始插手文艺,想把在文艺界威望很高的孙维世拉入手下,给她当参谋,合作抓话剧,又被孙维世婉拒。文革前,阶级斗争风雨欲来,毛泽东批评文艺界是“‘死人’统治”,江青见到孙维世说:“这下该到我家去玩玩了吧?”孙维世还是没去。为什么不去?她十四五岁和我母亲一起在上海学戏剧时,就认识了江青。那时,她的母亲任锐就要求她,少跟蓝萍那个女人来往。任锐怕女儿学坏。

维世与外祖父任芝铭1950年代在北京合影
维世对江青的无视,使江青明白,了解当年蓝萍的孙维世,很看不起她。因此,在对孙维世的羡慕嫉妒上,加了越来越多的恨。她要消灭所有可能阻碍她成为文艺旗手的人。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吵闹中骂过:“成元功是条狗!孙维世是条狼!”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听到过江青的这种叫骂,也听到过江青说要把孙维世关死在监狱里——曾经在江青那儿做护士工作的周淑英女士曾特意告诉我江青说的这些话,但没有听江青讲过“孙维世是美女蛇、狐狸精,是睡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这样一种表现女性吃醋心理的话。孙维世正直活泼、透明豪放的性格,也使所有认识她、接触过她的人,不会产生“蛇、精”一类联想。只有在不了解孙维世时,才会在略低一些趣味的作用下,发生这种想象。这种传说,或许是把文革中“刘少奇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定时炸弹”之类的语句,移用于对孙维世的叙述了。
此外,关于周恩来、邓颖超收养孙维世的事情,我母亲任均在口述史《我这九十年》中已经讲过。他们之所以收养维世,是因为,那是孙炳文、任锐的孩子。对孙炳文的几个孩子,周恩来抚养孙维世,朱德培养孙泱,我的大姨夫黄志烜认养孙新世。他们三个人是孙炳文生前好友,那时都认为抚育故友后代是一种责任。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现象,“赵氏孤儿”那会儿已经有了。我的外祖父任芝铭和他的同盟会友人,都曾抚养辛亥时期死难故人的后代,认为这种事情是责无旁贷的。外祖父也曾抚养孙炳文的次子孙济世,商震在抗战期间一直培养孙炳文的三子孙铭世。房轶五、房师亮父子曾掩护接纳任锐和她的孩子们。任锐的辛亥故友胡念祖和国民党员丈夫,在孙炳文遇难后,收留少年孙泱、孙济世,又受任锐托付,密藏朱德、孙炳文通信及照片等中共材料15年,至1950年寄送给朱德。在传统文化中,这些都属于“义”。受过这种熏陶影响的年轻人,后来政治道德怎样呈现,都是后话了。现在的文化没有了那种传统,所以没什么人理解了,乃至津津有味地去想象加引号的“特殊”关系了。
兰姐百年诞辰之时,我说一说想说的话,应该是对她的一种告慰。回顾孙维世极富才华的艺术人生,赞叹她的艺术成就时,更令人慨叹的,是她发挥艺术才华时间之短暂,空间之逼仄。艺术被极权政治宣传的工具性目的绑架后,艺术家被要求时刻惦记着为什么人,就再也无法专心开放性的自由探索了。直到文革祸国,造成了艺术的巨大苦难,和艺术家的深重苦难。创巨痛深,不可不知,不可不记,所以,在纪念孙维世百年诞辰时,一定同时纪念孙维世文革遇难53周年。
2021年10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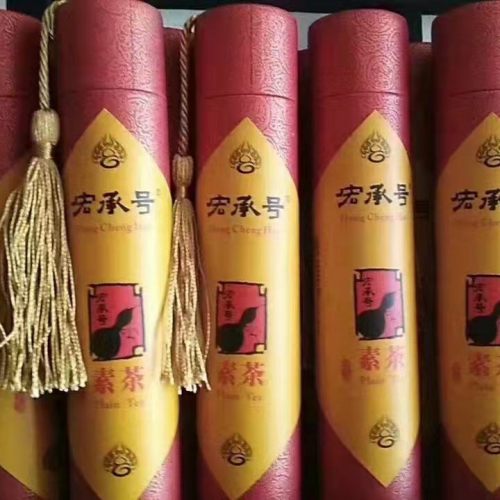
宏承号会客室
洞察社会万象,关注人物点滴。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