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邻右舍没故事

毛主席说:除了沙漠,任何地方都有左中右。
住在“高干别墅”也不例外。
我住的这套别墅原来是五室没厅一厨房,界开了之后分给我们四家住。
同一屋檐下,与人为邻,于是我也就有了左邻右舍。我住的一间半屋子加一个小小的储物间,屋门朝北;西面是一位秘书住着两间,屋门朝西;南面的单间住着一位单身女人,屋门朝南;我的东面邻居是位首长的司机,住着一个单间,屋门朝东。
由于屋门分别朝着东西南北开,每一家完全可以没有任何交际,可因为我们不管门朝何方,用的都是同一条电路,同一条水路,出入走的都是我门前那同一条小路,这交际也就不得不发生。虽不是天天见面,打个照面是常有的。
人与人的交际会因为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用意,而有不同的故事。
交而为善是大部分人的想法,可这个世界上人太多,想法也就太多,就有人并不是从善如流,而是抱着高人一等的心态看待别人。
出乎我预料的是,住进“高干别墅”的第六天,我就被组织上派到北京参加一个学习班。更出乎我预料的是,在我学习的一个月中,别墅里发生了不少离奇的事情,有些是直接针对着我来的。我不在家,矛头便全集中到了我妻子的身上。
我出差走的第三天夜里,住在我家隔壁的那个秘书,就气势汹汹地跑到我家里,说由于我家用电过多,造成了他家的电闸总是自动脱落,为了使这种现象不再发生,必须把我家的电给断掉。
妻子刚从农村来到省会级的大城市,坐在屋子里都战战兢兢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她不敢有丝毫的违抗,看着自己家的电闸被别人毫无道理地拉下,她除了晚上点燃蜡烛,没有作任何争辩。
电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没过几天那个秘书家养的一条狗,又狗仗人势把妻子的腿给咬了一口,并且是在我家门口咬的。

那天妻子刚锁了篱笆门要上街去,转身的时候,秘书的老婆牵着一条狗也要出去,妻子站在门口让她们先走,那条狗在走到妻子跟前时,呜的一声就向我妻子扑来,妻子躲闪不及,腿被它咬了一口。
秘书老婆不但没有说一声对不起,还想扬长而去。妻子和她讲理,她却爱搭不理。没办法妻子就把这事告诉了我的领导,领导出面找秘书,让他带我妻子去打狂犬疫苗。没想到秘书也很蛮横,领导就把这事反映到了首长那里,首长看事态严重,出面调停,他才带着我妻子去打了狂犬疫苗。
我从北京回到合肥后,妻子并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是一个邻居说起我才知道的。
我听了非常生气,要去找秘书理论,妻子却拦着我说:“已经没事儿了还提它干啥,以后都住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让他几分又何妨?”
我说我可以不找他,但我必须要让他领导知道他的德行。不料和我同样气愤的同事又拦住了我,说:“别找了,你住在那儿以后就会明白的。他既然敢这样狂,是背后有人撑腰,撑腰的那个正是你想找的人,你说你还能说得赢吗?”
同事的一番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不明说,但从他的欲言又止中,我似乎嗅出了一点什么。
我们都是部下,凭啥有人只给秘书撑腰?我想不明白,但不久后的一件事让我疑惑顿消。
那是初夏的一个上午,我正准备出门,隔着窗户玻璃看到那位“撑腰的人”正向我住的方向走来,是来找我的吗?我准备开门迎接,但手抓到门把手那一刻却犹豫了,他是不是来找我的呢?许找别人的呢?班时间这个院子很少有人在家,他今天为何一个随从也没带独自来这里?在平时是少见的情况啊。
于是,我准备开门的手放下了,透过窗子静静地看着他的身影向这边移动。他的神情显得有些神秘兮兮的,走近我的小院时还向院内看了一眼,然后又从我的门口走过向西而去。
我松了一口气,果然不来找我的。不一会的工夫,我听到了隔壁有开门的响声。接待“撑腰人”的是那家的女主人,男的显然不在家。一开始还有声音,渐渐地,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只有门外梧桐树上的小鸟在歌唱,还有母鸡与公鸡嬉戏时的欢叫声,远处偶尔有汽车鸣笛传来,但很快就消失了。此时,世界变得异常安静。我突然没了外出的打算,眼睛盯着院里的那两棵枇杷树。枇杷果已经开始变黄,但我始终没听到弹琵琶的乐声响起,看来名字与实质是不能简单联想的啊。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隔壁又传来开门声和关门声,接着是那个熟悉的背影从后面的小路上走了出来,没人相送。背影边走边左顾右盼,当然还向西院看了两次,然后渐渐消失了。
他离开不久,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少妇也从小路那头出来了,一袭翠绿色的长裙,把身段张扬得轻飘飘的,遮阳的宽边帽上,有朵红花分外耀眼。这女人曾经是那么的傲慢,现在依然傲慢。若有所思后,我愕然,我释然。
此时我明白了同事让我忍一忍的话外音。
单身女人的屋里是很少有声音的,她与我的屋子原本有一条走廊相通,是一堵墙隔开了相连的两间房,她居南我居北,形成了天然的背靠背。除了因为土地发生过一场“战争”,再没有别的交往。
而我东面的邻居是首长的司机,司机姓王,是名志愿兵,和我同年入伍,人憨厚、聪明,一看就是能靠得住的人。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父母也跟他们一起住。
在我们四家人中,他的住房最紧张,一间房子住祖孙三代六口人,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就那样在一间屋里住着,直到我在院子里建起“违章厨房”之后,他看没人纠察我的“违章建筑”,就也在自己的屋门外搭起了一间伙房。
他的伙房比我的建的稍大些,建起之后里面除了做饭还放了一张床,看来那不仅仅是一间厨房了。
我们是同年兵。我叫他老王,他一家是安徽人,非常客气,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送到我家让我们品尝,每逢过年我们会一起吃顿饭喝两杯。
老王的父母没多少文化,但他们说起祝福的话来,张口就来,一串一串的,不但词儿多,说得非常顺口,令我佩服至极。由于老王家的孩子叫我叔叔,孩子的爷爷奶奶居然也跟着叫我叔叔,这让我很长时间不适应,因为河南并没有爷跟孙叫的习俗。
他家新盖的厨房在我卧室的东窗外,紧邻湖岸,湖边有一棵凤凰树,到了夏天,树上好像每片树叶都是一只知了,蝉鸣声此起彼伏,睡觉都要用棉花堵上耳朵。
可这些知了的叫声与老王家儿子敲打出的响声相比,用现在的话来说,真是弱爆了。他儿子三岁多一点,夏天无论再热他都是不睡午觉的,好像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手拿铁棒到处敲,每天中午都把破铁盆敲得山响,我在床上想睡着是不可能的。那时我屋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不能关窗子,不然屋里太热。所以他没完没了的打击乐仿佛就在我的耳边敲,有时吵得我想上吊的心都有。
虽然心中很烦,可我没有给老王提起过,一是他们见面就先道歉,说儿子不懂事儿,肯定吵着您了;二是毕竟那是小孩子,小孩子不乱敲那就不是小孩子了,我也是从小孩子时候过来的,曾也这样让大人烦恼不已过,大人若和孩子计较那就不如孩子了。当然吵我睡午觉的不光是知了,也不光是老王家的儿子,还有我家那些母鸡们,它们好像专在中午下蛋,有意和我对着干。可它们是鸡,我没有权力让它们先憋着,等我睡完午觉再下蛋。
我的对面住的是高干的遗孀,带着她的女儿和女婿一家三口人,不愧是高干之家,文明有礼,平时很少听到他们家有吵闹声,周日除外。每逢周日她的儿子就会带着老婆回到别墅来,三口人增加到了五口人。
她们一家人聚到一起的唯一爱好似乎就是打麻将,一桌麻将需要四个人,他们就会多出来一个人,每次都为了让谁多出来而争吵不休。等打完了麻将声音更大,因为清算赌资的时候,欠一毛两毛都互不相让。一旦等钱结清了,又是和和气气的一家人。
家有左邻右舍,人有三朋四友,生活有酸甜苦辣,家庭有和和睦睦,是件多么惬意的事啊。当然不排除会遇到个别恶邻和损友,遇上了也没必要烦恼,因为有了他们,你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想想活在这个繁杂的社会里,一生都没人惹你生过气,那你的人生该是多么的乏味啊。
所以我常感谢那些对我有恩的人,感谢那些在我面前无事生非的人,甚至感谢那些曾经诋毁我的人……

张国领,河南禹州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78年入伍,2020年退休,历任战士、排长、新闻干事、电视编导、《橄榄绿》和《中国武警》杂志主编,从军四十三载,武警大校军衔。
主要著作有诗歌、散文集《血色和平》《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和平的欢歌》《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柴扉集》《意外的爱情》《张国领文集》(十一卷)等十八部。作品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群星奖”,“长征文艺奖”“冰心散文奖”“武警文艺奖”等五十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新时代强军文学作品选》《军旅年度文学选》《中学生喜爱的作文》《初中课时练》《改革开放四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选》等六十多种选本。系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丰台作协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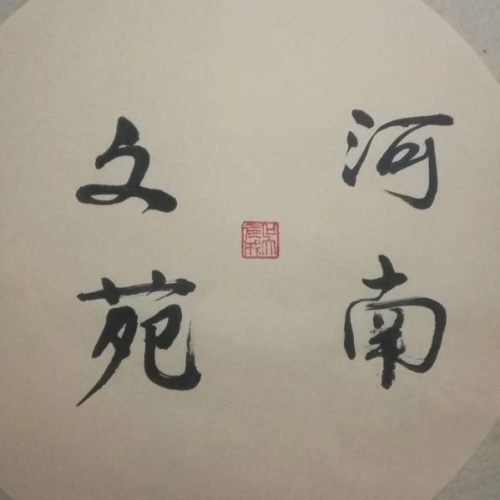
河南文苑
河南文苑官方正观号
最新评论

河南文苑
👍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