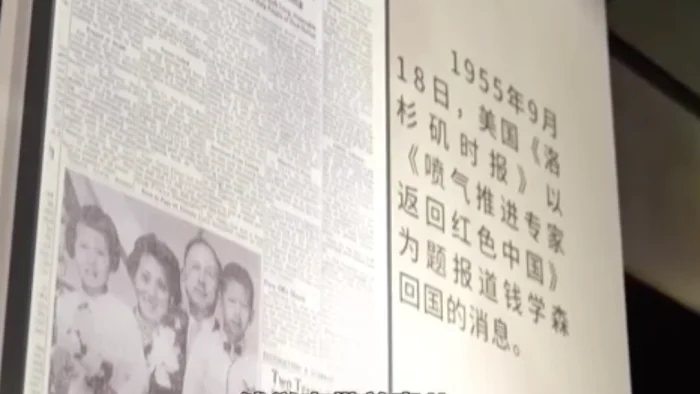一进门就见到旁边柜子堆满了中外摄影类书籍,走到大厅,又看见一些很专业的补光拍摄设备。左边窗台旁放置一张欧洲古典韵味的茶桌,两张矮沙发看起来很软,坐上时脸被窗外的斜雨扑中,酥痒痒的。秋天淡淡的凉意混合一种特有的雨中泥土与植物的香气从窗缝传进来,李英杰熟练地挑选颜色适合的幕布,他偏向右侧的短发干练精神,戴着暗红色框架的眼镜,“黑色背景怎么样?”62岁的李英杰说话中气十足,整个人充满精气神儿。
茶桌的对面是一个仿古的柜子,柜顶放着一些摄影界如“中国摄影金像奖”之类的重量级奖杯,柜中放着各种款式的相机,沉淀出岁月的微微光泽。

李英杰,中国当代摄影家,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长期致力于黄河文化与东方哲学的影像表达。他耗时15年三次走完黄河全程,创作《黄河纪》系列,以6万余幅作品构建“活着的民族史书”。作品多次在法国、日本等国展出,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出版《太极》《黄河纪》等专著,其中《太极》获“中国最美的书”称号。

《太极三部曲》——用摄影诠释太极
正观新闻记者:是什么契机使您走上了摄影之路?
李英杰:我上大学时就是个“文艺青年”,那时候爱写书法,还获过奖,后来为了记录生活买了照相机,真正专业创作是从2006年到禹州市工作以后开始的,拍钧瓷、具茨山岩画。我2008年加入的中国摄影家协会。
正观新闻记者:请结合您的《太极》系列创作,谈谈您是如何用“光与影”诠释太极哲学的?
李英杰:我用了12年的时间完成了《太极三部曲》的创作。
太极是中国古人辩证的哲学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富独特性的文化遗产之一。
李英杰谈《太极三部曲》
太极三部曲第一部《太极拳》,是以慢速摄影的方法,把通常人们看不到的打拳者的能量轨迹记录了下来,形成抽象图式,用抽象抵达一些象征意义,也是在宣传我们的太极文化。

整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但第二部《太极图》难度大——为了拍一张经典的太极图,我在温县一个废弃工厂搭了9米多高的脚手架,晚上拍,6个人配合,前后用了6个小时。
拍太极图是因为,我认为太极理论与太极图是象数和义理结合的表达,也是对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最简明的表达,因而能代表中国固有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
“一阴一阳之谓道”,我的拍摄是对太极的文化体验。长时间曝光成像后,删繁就简,在作品中表达出太极拳的内蕴,留下了飘逸的太极行迹图。以动静、快慢来表现太极图的黑白、虚实,以太极的方法拍太极。

通过摄影语言阐释的太极图像,作品呈现的艺术精神,正如道家所崇尚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这些图像都是一次拍成的 ,后期的调图除影调外没有做任何改动。

我拍的太极三部曲第三部是《河洛象》,河图、洛书是古人对天地自然、宇宙时空、地理认知,以及自身存在的切身观察与感悟。可以解释为:河图本是星图,其用为地理,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洛书是关于空间的表达,包括东、西、南、北方向。河图、洛书的图式还反映出中国人对数字的崇拜及时空观念。
我生活在河洛地区,受河图、洛书的启示,走过河洛、南海、西藏、欧洲、北极,用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并以科学为佐证,探索星空宇宙图景,与天地自然对话,寻找文明的心灵图像,演绎出一部当代的河图、洛书。
以上这些图像都是直接呈现一次拍成的 ,后期的调图除影调外没有做任何改动。
《太极三部曲》是我用摄影表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东方视觉观探索的例证。

正观新闻记者:第三部《河洛象》您提到“用水拍天象”,这是怎么想到的?
李英杰:河图洛书是古人观天象画的两幅图。我参考哈勃望远镜拍的星空图,在海南三亚、黄河边拍水的漩涡、波纹,用抽象的水痕模拟天象,算是当代版的河图洛书。在三亚拍时,没注意涨潮,拍完回头一看,已经被水包围了,最后扛着三脚架、相机,踩着到肩膀的水才出来,现在想起来还捏把汗。

正观新闻记者:这组作品后来获得了什么奖项?
李英杰:2014年拿了第十届金像奖,艺术类排名第一。投票时分数一直领先,评委认可我“用西方摄影技术表达中国源头文化”的思路——这些作品都是一次拍成,后期只调影调,没改像素,算是“直接呈现”的艺术表达。
正观新闻记者:您认为摄影这门艺术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与改变?
李英杰:接触摄影之后我深深爱上了它,为了拍出好的照片,我常年去户外,冷热天气很多,增强了抵抗力,也经常晒太阳,走路爬坡也是运动。也因为这些常年的户外拍摄,我现在62岁了身体还很好,没有“三高”,感觉自己正在人生的黄金阶段。
可以说我酷爱摄影,刻在骨子里的热爱。现在,我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摄影上,包括摄影创作、后期修图、学习摄影知识、探索新的摄影可能,等等。
用摄影探索AI与未来
正观新闻记者:AI现在可以直接生成任何我们想要的图片,您怎么看待这种艺术的真实?
李英杰:AI图像生成技术颠覆了传统的创作模式,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和应用AI。AI模型是在我们人类集体创作的海量数据上训练而成的,因此,AI生成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集体视觉文化和审美偏好的提炼与映射。
李英杰谈AI
我认为,AI并没有消灭艺术的真实,而是重新定义了“真实”的维度,将它的重心从“手艺的真实”转移到了“意图与观念的真实”。真实在于人,而非工具。艺术的“真实”最终不在于工具本身,而在于使用工具的人。
而AI艺术的“真实”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前端的真实。它包括使用者的意图、审美、创意和叙事能力成为了核心。一个精妙、复杂、充满隐喻的提示词,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独创性的思维创作。它的“真实”在于创作者独特的思想和视角。
一个是后端的真实,从AI生成的海量结果中筛选、编辑、组合、赋予意义的过程,体现了人的主观判断和审美决策。这就像摄影师在无数瞬间中捕捉决定性的那一刻,策展人在众多作品中构建叙事线。
对于评论影像作品,应该把AI和非AI作品分开,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
正观新闻记者:您未来有什么新的创作、展览计划?
李英杰:一是继续创作《黄河纪》,争取再用两年时间,出版《黄河纪》书籍。当然,黄河是一个长期的主题,我会一直关注。我还想拍一下世界排名前十的河流,分别是:尼罗河、亚马孙河、长江、密西西比河、鄂华-俄尔齐斯河、澜沧江-湄公河、刚果河、勒拿河、黑龙江。当然,这些河流的拍摄不会像黄河这样,是一个大致的记录。二是《时间》的创作。三是《太行山》、《伏牛山》的创作,这些作品已经有了基础。
《时间》我想用水、雾、云等特殊摄影语言表现流逝感,比如流云、急流;《太行山》《伏牛山》之前拍了不少,有感情,想补拍些季节限定的场景,拍完出书、办展。
15年,3次,25万公里,1000多个黄河人的故事
正观新闻记者:请您结合您的《黄河纪》说说,三次行走黄河的故事。
李英杰:我生长于河洛地区,黄河岸边。正是黄河的文化、黄河岸边劳动者身上那份特有的坚韧与淳朴,深深打动了我,促使我拿起相机,决心将他们记录下来。
十五年间,我三度全程行走黄河5464公里,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拍摄黄河人的环境肖像、日常劳作与生活场景,大概有1000多个人了。我也在探索新纪实摄影方法,也试图记录下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图景。这一路,我见证了黄河生态的变迁,也定格了黄河儿女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瞬间,形成摄影作品《黄河纪》。
李英杰谈作品《黄河纪》创作过程
正观新闻记者:您一般什么时间出发?路程始终点是?
李英杰:一般我会选择秋天出发,因为秋天雨季过了,不耽误赶路,还能拍收割场景——9月到10月,黄河上游收玉米、割麦子,热闹得很。
第一次走了3个多月,后两次各一个半月,从郑州出发,先到入海口,再往上游走,经青海鄂陵湖、扎陵湖、四川九曲黄河第一湾、甘南、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最后回河南,九个省一个不落。
正观新闻记者:这一路吃住怎么解决?费用高吗?
李英杰:住的话,县城、乡镇有宾馆就住,偏远地方带车顶帐篷,偶尔还能借宿老乡家;吃饭自己带锅碗瓢勺,电车能烧水做饭,没条件就吃方便面、火腿肠。新能源汽车一公里耗费3毛钱,一天吃住行200块左右,比胶卷时代省钱多了。
正观新闻记者:拍的这些黄河人中,有没有印象深的故事?
李英杰:有个青海的大学生,两口子都是郑州一所水利大学毕业的,回青海开拉面馆,我拍过他们。后来他们家地震,饭馆塌了,还发照片跟我聊,我看着也难受。好在政府补了钱,现在馆子重建好了,还创新了拉面口味。
还有个山东大学生,在河南租200亩地种粮,经常跟我交流,都是萍水相逢,但能一直联系到现在,难得可贵。
正观新闻记者:您的《黄河纪》是怎么构思出来的?
李英杰:我拍黄河,从六个方面考虑,有人文,有自然,主要偏重于人文。
一是黄河道。我拍黄河,从它的“九曲”河道开始。这百转千回的景象,就像我们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大河雄壮又充满母性,人与这壮阔的景观早已融为一体。这是我的“黄河交响”的序曲,从这里,我找到了讲述它的方式。


二是黄河景。镜头拉近,我看到了人在大地上的痕迹,感悟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耕种、放牧、祭祀、劳作……生于此,归于土。沙漠、绿洲、湿地、麦田,人改变自然,也依赖自然。风景里是故事,文明就在这自然画卷上由人一笔笔描绘。

三是黄河人。人是主角。一切表达,最终都是人的体验和感受。我拍黄河人,既有他们劳作的瞬间,也有环境中的肖像。他们的表情、姿态、穿着、背景,讲述着普通人的生活,也透露出我们共同的血脉和文化根基。通过这些面孔,我看到的是整个民族的生动样本。

四是黄河情。我记录社火、祭拜、节庆活动,不只是拍热闹,更想捕捉其中中国人特有的相处方式和生活态度。黄河文明自古就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份世俗化的温情,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东西。

五是黄河工。那些宏伟的水坝、发电站、控导工程、铁路大桥、公路大桥,是人类试图征服黄河的见证。治水,自古就是大事,关乎生存与安定。我拍下它们,思考着:征服自然固然展现了力量,但如何与它和谐共生,或许才是更深的智慧。

六是黄河象。最后,我用抽象的方式,拍黄河奔流入海,水天相接的壮阔景象。它也是黄河的肖像图。像一首交响乐的尾声,带来的思考——关于这条河,关于我们与它的关系——却绵延不绝。


正观新闻记者:您有没有遇到过极端天气下的拍摄,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危险?是怎样的情境?
李英杰:在黄河入海口,零下20度无人机遇大风,飞了3800多米就失控,最后摔冰面上,修理花费1万多元,无人机品牌方承担一半;在扎陵湖拍摄时,晴天突然下大雨,无人机自动返航才没掉湖里;海南那次最险,涨潮困住了,一开始想打110,后来试了试水深,到肩膀能走,就扛着设备慢慢挪出来——那次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正观新闻记者:您这些年从农耕文化入手,记录和表达了黄河多元文化,甚至揭示了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能举例说明吗?
李英杰:整个拍摄过程,同样也是一次观察与发现的旅程。我不可避免地记录并直面了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下面,举几个例子。
黄河滩区的镜头里,记录着农村的深刻变迁:老村庄被拆除,农民们告别旧居,迁入由国家巨资兴建的新型社区——有的搬进县城周边的安置楼房,有的入住乡政府附近的联排别墅,有的则安家于就近抽取黄河沙筑起的高台之上。此举腾出了大片土地,也让村民的生活、就医和子女就学更为便利。然而,新的家园虽新,世代耕种的土地,却实实在在地远了,住进高楼不适应,生活成本高,院子变小,机器农具无处放置等,进步并非坦途,便利也需代价,而人与土地那千丝万缕的牵连,总在镜头里记录。
一些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求职遇阻后,选择回到农村投身农业。这些知识青年的回归,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带来先进理念、创业抱负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在牧区,同样能看到类似的身影。这群充满活力的新农人,正是农村发展的希望所在。但是,在与这些人交谈中,也明显感到他们向往城市生活。
透过镜头,我看到黄河滩区土地的变化。一方面,自从农村分了责任田,人过世后难进祖坟,大多就埋在了自家田里。留下的坟头越来越多,挡着大型收割机下地作业。
另一方面,生态改善了,鸟多了,庄稼受到侵害,给农民种植带来了麻烦。农民绑扎稻草人,吓唬鸟儿,有的农民甚至用农药把鸟药死挂起来,吓唬同类活鸟,这是生态与农业发展中的矛盾。

正观新闻记者:您在拍摄《黄河纪》前,做了哪些知识储备?
李英杰:在《黄河纪》拍摄之前和拍摄过程中,一是学习世界摄影史和主要的摄影理论书籍,明白自1839年达盖尔发明摄影术以来,摄影发展的进程、脉络,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二是学习研究了黄河文化、社会统计学、调查学有关方面的知识。比如,阅读了许倬云《万古江河》,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陈缵汤《密西西比河探游》、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温县统计年鉴2010-2023》等十几本书籍。三是阅读参考了萨尔加多的《创世纪》系列、《萨尔加多传》、《艰难岁月--爱德华·斯泰肯眼中的美国农业安全局影像》》等画册,兼收并蓄,为己所用。
“我的黄金岁月刚刚开始”
正观新闻记者:回首数十载,有没有关键性的机会,您是如何把握住的?
李英杰:我比较幸运,遇到了这两个给我极大灵感的素材。我生活工作在黄河岸边,河洛文化的核心区,这对于我拍摄太极文化、黄河文化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黄河文化、河洛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一定要抓住机会。我现在对外发布的是两个专题作品,一是《太极三部曲》,二是《黄河纪》,都是黄河文化的作品。
正观新闻记者:有没有使您受益匪浅,坚持了很久的好习惯?
李英杰:那可能就是找准方向,然后坚持。太极拍12年,黄河拍15年,中间遇到困难就解决,没想着放弃。比如一开始拍太极总拍得太“实”,试了频闪、月光下拍、烟雾里拍,最后才找到慢门的方法。年轻人不管搞什么,选个好专题,坚持下去,再找独特的表达方式,肯定能成。
正观新闻记者:在摄影界,您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没有哪些人生经验,分享给后来者?
李英杰: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有一些体会。一是学习,二是思考,三是坚持。我是一个幸运者,人到中年又拾起来了青年时的爱好,还能获得认可。现在摄影就是我的工作,它能给我带来收入,同时,它也是我的热爱,拿起相机出去拍照,找角度、等光线,出片时非常激动,晚上回来再修图、剪片,也觉得很有意思,一点不觉得累。
摄影让我每天都感到充实、快乐,我觉得自己一直奔走在人生幸福的道路上。
(文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岳炎霖
统筹:石闯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