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桦
夫藏书印者,典籍之眉目,藏弆之信证也。其源肇自三代玺印之制,初为取信之物,秦汉以降,渐入缥缃。今以篆刻与艺术史之眼观之,方寸之间,岂惟钤记归属?实乃文脉流转之迹、艺心匠意之凝也。兹述古今之变,聊陈管见。
一、滥觞与初兴:藏书印的早期形态(先秦至唐宋)
昔者《周礼》载“玺节”之用,官民以印为信。秦制严玺之名,唯天子独尊;汉廷广章之秩,颁于将守。唐时称“宝”崇帝玺,别以“记”“关防”区官私。此皆印信制度之演进也。
及至藏书之风兴起,印文才真正与书籍结合。六朝隋唐时期,写本珍稀,藏家开始钤盖名号印章以杜绝伪作和散失。例如李唐内府的“弘文之印”、宋元书院的“某某藏书”等,都已初具规模。
当时的藏书印尚显质朴,印文多采用篆隶字体,布局严谨规整,很少进行刻意的雕饰。这是因为印章的主要用途在于征信,其艺术价值尚未得到彰显。
二、鼎盛与成熟:明清藏书印的艺术化转向
明清两代,典籍日益浩繁,藏书之家层出不穷。像绛云楼、汲古阁、天一阁等藏书楼的主人,不仅聚书万卷,更以精于鉴赏而闻名于世。藏书印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风雅之事,形制也变得纷繁多样:有的题写斋堂馆阁之名,如“知不足斋”“士礼居”;有的抒发个人志趣襟怀,如“曾经我眼即有缘”“得者宝之”。
印文的篆法上,兼收古文、籀文、虫鸟篆等不同字体;章法布局上,有的疏朗如星汉,有的密致如云锦。黄丕烈的印章隽永流丽,杨继振的印章奇崛古拙,都与其本人的藏书性格和品味相契合。
与此同时,篆刻艺术也已臻于成熟,文彭、何震等篆刻家以刀代笔,使得藏书印焕发出金石之气,在方寸之地展现出开阔深远的意境。
三、转型与挑战:近现代藏书印的学术化与式微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古籍保护的学问开始萌芽。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对藏书印的鉴定与收藏进行了论述,开创了藏书印研究的先河。但由于战乱频繁,旧藏散佚,印文的释读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技艺。
近二十年来,古籍普查工作大规模开展,李国庆、吴芹芳等学者致力于印文考释和递藏关系梳理,或在细微之处辨别真伪,或从残缺的钤印中钩沉往事。相关著作如《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印选编》等,图录丰富,尽管释文间有错误,但保存了近万枚印章的影像资料,功不可没。
然而,在当今简体字环境下,识读篆籀异体字如同涉足深渊,辨别增减笔画的变化更如分辨星雾。青年从业者往往望印生畏,这实在是传承古代文化所面临的困境。
四、机遇与路径:数字化时代藏书印的传承与发展
今人研习藏书印,主要面临三个难题:一是著录缺乏规范,各馆的释文存在差异;二是人才凋零,同时精通篆刻与文献学的复合型人才稀少;三是资源分散,各数据库之间相互孤立难以互通。
但科技的昌明或许可以弥补人力的不足。如果能建立钤印元数据规范,用数字技术拓印印章形态,用人工智能辅助释文,并进一步关联印主、藏本、递传链条,那么方寸之印就能构建成一张知识网络。古人云"印为心画",如今应当用数字技术延续其生命。
不过,技术终究只是工具,艺术的根本在于人。篆刻之道,贵在刀笔相生、意趣超然。希望后世学者既能学习释读的技艺,又能修习金石艺术,使藏书印不仅成为考据的资料,更能延续刻石的精神。
结 语
从青铜钤信到纸墨藏印,千年文脉镌刻于方寸之间;从官府典守到私家珍玩,百代风流凝聚于此小小印章。纵观古今,藏书印岂止是典籍的附庸?它实在是华夏艺文的缩影。若能统一规范、培养专才、融合科技、彰显艺术,那么这朱泥小印必将与缥缃万卷一同光辉不朽。
2025年9月18日于寄吾斋
(作者:温州市方介堪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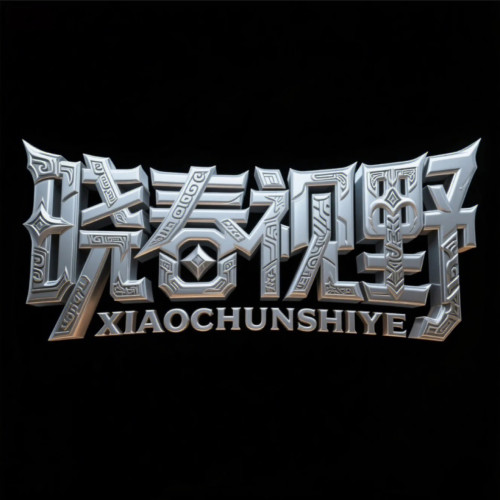 晓春视野
晓春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