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入窗,素纸在案,墨味氤氲,灯影摇曳。堂中挂两轴行草,旁设写意花影。观其线,劲若铁丝,活若游龙;观其势,起落如山,回环如水;观其墨,或浓或枯,或湿或燥,四象互生,气息在焉。纸面之中,字字独立,行行相望,牵丝如琴弦,方寸俱成丘壑。

再近一步,锋意外露,提按有节。起处逆入,行处中锋,收处回裹;疾则霹雳,缓则行云。粗者为骨,细者为筋;枯者露锋,润者藏力。偶见飞白,恰如雪光入夜,清而不寒。此非轻佻之笔,乃从碑学中来,以金石厚拙,托草意纵横。于是欹与正相生,险与稳并处,章法起伏,如岭之绵延。
陈叔亮之书,于吾观最贵“气”。气不在声势之大,在脉络之通;不在一时之惊,在通篇之和。观其大字突起,如峰插汉天;小字相衬,如溪穿松壑。空白处不空,皆为气口。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眼随笔走,意与气行。此等铺陈,非仓卒所得,必由经年之磨、寸心之守。相关评誉屡见,称其自成面目,信手成章;言简义赅,恰中肯綮。


再看对联,笔缓而重。转折处似迟而实稳,点画如石,如斧凿痕。此中有古陶之质感,亦有钟鼎之气味。块面并列,重心低稳,朝揖俯仰,姿态端庄。由此而返观行草,则草书不飘,筋骨不散。金石之力,正为草意之舟楫。
移步花鸟,秋实累累,藤蔓缠空;荷叶舒展,水光粼粼。其画以书法入笔:藤线为牵丝,叶团为浓团,叶缘飞白显锋,花蕊钉头显劲。破墨处云气蒸腾,叠加处色阶层现。款识不作附属,反为画中节拍:或长或短,或疏或密,与印同参,收束全局。此乃“书画合参”之法,尤见功底。
诗心贯通其艺。吟咏之间,格律严整;意在胸次,或朴或壮。边塞感怀,入书成雄强之势;山阴题咏,入字成清潇之韵。诗为气源,书为骨干,画为肌理,三者互济。诸名家所许,谓其“手眼相应,见性成章”“文章天然,妙得其趣”,皆可据此解。
又记一事:昔年经典剧作启幕,一“西游记”三字,出自其手。草意飞动,碑意沉着;方寸之间,气吞风云。群贤初识此字而识其人,艺林之外亦记其名。是知传统笔墨,若得其度,亦可与众共享,入千家万户;名与艺并传,雅与俗同欣。


细绎其法,可撮其要:以诗练气,持久吟诵,使胸次有节律;以书立骨,潜心碑帖,使线条有重量;以画达意,直面万象,使情境有依凭。三者同修,日久弥坚。临池之际,当先求“稳”,稳而后快;快亦不浮,必由稳生。用墨之际,宁可略枯,以见锋骨;润则慎用,以防滞气。结体之际,避平,取奇;奇亦有度,须以顾盼成势。章法之际,避散,取合;合亦有变,须以空白通气。此诸条,非条陈之法门,乃观其作品而自悟之理。
回望全局,其书有山川之形胜:峰峦起伏,江河回环;其画有四时之气息:春风潜入,秋光泛金。古意并非沉睡在故纸,乃在当下呼吸;法度并非束缚手脚,乃使手脚有力。以此见其人:不以繁饰取媚,不以怪奇争胜;从容把握,胆识与修养同行。
诗、书、画,本是一家。以诗摄气,以书成骨,以画见象。陈叔亮所示,正是此道的当代注脚。观其行草,听风起于毫端;观其花鸟,看水光从墨里涌出。古与今、雅与俗,于是相逢;法与情、骨与韵,于是并行。此可为学书学画者参照,亦可为爱美之人把玩。手捧其作,如握一段山川,如听一阕清歌,久久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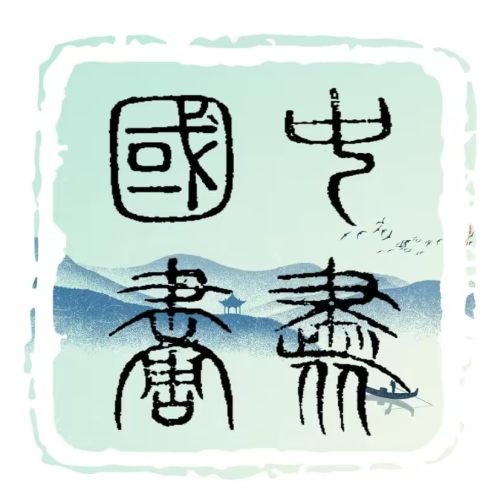
中书国画
中书国画官方正观号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