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有声,风入旷野,草色在云根间浮沉。马影并行,蹄声断续,天地阔远如初。艺林多路,或炫耀以奇,或驰逐以巧;而有一人,守清守简,以诚养笔,以静驭墨。观其画,知其心;听其线,识其骨。工以立形,意以安神;色不求繁,调自成章。广野低回,云幕如涛,人物与鞍马同在风影里,若行若停,皆含分寸。

孙志钧少岁即与丹青相亲,临摹勤谨,白描沉着。及入学院,素描、透视、体块、解剖,层层积累,根柢深厚。既出校门,不逐喧竞,不迎新潮,独于草原情思反复沉潜。昔日牧场岁月,风雪连年,三人分工,或放羊,或做饭,或守夜;月轮一转,岗位轮替。辽天无际,烟火难逢,寒气浸骨;长久凝望,山影入怀,云声入耳。此等经历,化入笔端,化入气格;后来画马画人,沉稳不躁,朴厚不饰,皆本源在此。
观其工笔,线若筋,转若枢。提按分明,顿挫有致;简而不薄,松而不散。形体之中,关节、受力、肌理,隐若可寻;整体之外,势与气交互扶持。设色多取固有,少为铺张。蓝灰、赭灰、墨灰递进相和,冷暖不争,层次自显。背景多留清气,用少量晕染承接人物与马群,使画面显深而不滞。此法不逞繁华,而能久视;不取光怪,而能远传。


及至水墨写意,思路更开。大刷破墨,肌理如沙,如霜,如风起草尖;大片留白,与浓黑相抗,节奏鲜明。人物少笔,马形简笔,然势能充沛;提笔一转,便见奔突;收笔一敛,便得静候。广角俯仰,视域尽展,地平线与云带相向;远山若隐,近地若伏。观者立于画前,不觉身入风口,衣襟微动,耳畔似有马蹄回响。
其构图多用两法:或以大空衬小形,阴阳对照,使长风得以通行;或以近距斜角摄动势,黑白叠映,顷刻聚力。人在画里,不过几笔、数面,然神情自存;马在画里,不过数形、数点,然筋骨自成。此处功夫,不靠花巧,全凭写生。对景写生多年,寒暑不辍;关节处何以转,肌肉处何以起,皮毛处何以亮,皆烂熟于心。故能以简御繁,以少胜多。
其色不艳。常以一二色系统摄全局,或蓝灰护天幕,或赭灰护地脊;少量高纯度小色点,如火如星,点醒叙事。冷暖对比有时加大,然边界以雾化收束,令强烈化于温厚。久而久之,画面呈现一种“记忆调”:像旧梦回潮,不刺眼,不喧闹,惟其深。


题材虽专,不觉局促;格局虽静,不失灵动。草原并非只是地貌,更是秉性。孤而不怯,简而不枯,耐受而不僵。人物在此,面貌不刻,精神自明;马群在此,毛色不繁,气象自足。画里讲述,不为故事,不为传奇;只把一种活法安放于纸。风来,影动;雪至,声沉;朝暮之间,生命有厚度,时间有重量。
其所以能长,是因“真”。写生真、情感真、取舍真。画里不夸张,不刻意;画外不争名,不逐利。回看多年积累,一条脉络清楚:以工笔立形,以水墨立气;以草原立意,以现实立品。人、马、风、云,四物相依,四气相和。观其近作,更趋寡言;一纸黑白,万里长风;无须繁辞,足以动人。
人或问:“既强写实,何以终抵诗性?”其答在两端:一在生活,一在节制。生活给予沉厚;节制带来留白。沉厚使画不漂;留白令意可远。于是,具象不再仅为具象;黑白不再仅为黑白;形体与节律交织成新秩序;叙事与象征会合成新含义。观者初见马与人,再看风与云,复看胸次与气度。如此三看,方觉余味在纸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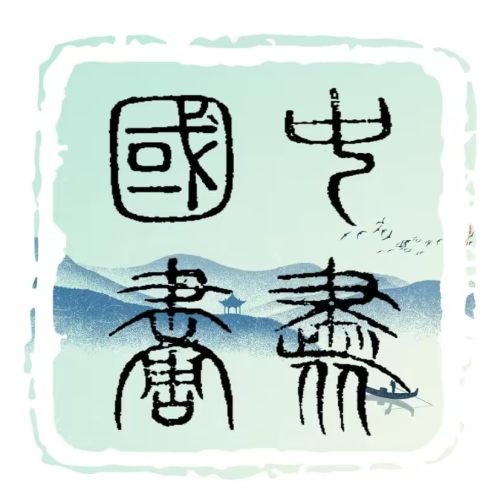
中书国画
中书国画官方正观号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