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观新闻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闫洧涛
登封与新密交界处的山坳里,弋湾中学的旧址早已湮没在矿区的尘烟中。断壁残垣间杂草疯长,唯有风穿过破败窗棂的声响,还在复述着一个名字——王保才。这位从新密翟沟走出的教育者,以四十年粉笔生涯为刻刀,在贫瘠的乡土上雕琢出教育的奇迹。从王村乡小学的初登讲台到大冶乡沁水小学的执掌帅印,他用板书的力道,在黄土地上写下“希望”二字。在资源匮乏的年代,他是弋湾教育的拓荒者,中心校“掐尖”抢生源,他就带着教师在油灯下补课,让村办中学的中考成绩连年领跑开封地区;面对农家娃“跳出农门”的渴望,他是执着的摆渡人,每年将一批批学生送进中专、高中的校门,让知识改写命运的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于坚守与奉献中,他更像不灭的灯塔,1956年入党的誓言化作光束,照亮了乡村教育的崎岖路。如今矿区的机器声盖过了当年的琅琅书声,但那些从弋湾走出去的身影,那些被他改变的人生,都在印证着:有些东西,远比砖石更坚固,比岁月更长久——比如一位教育者用初心写就的“不褪色”的传奇。

红根:窑火照初心,少年志如钢
1933年8月,密县平陌乡翟沟的土窑洞里,一声婴儿啼哭划破了夏夜的闷热。王保才降生时,家里已有好几个弟兄,炕上铺着的破麻袋根本挡不住潮气,母亲只能把他搂在怀里,用体温驱散初秋的凉。
1942年,豫西大旱,地里颗粒无收,本就拮据的家彻底撑不住了。看着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孩子们,父母咬着牙托四爷的亲戚帮忙——在卢店给孩子们找条活路。9岁的王保才跟着亲戚走了三天,脚底板磨出了血泡,最终却被送到了地主杨仓家。
在杨家的日子,是刻在骨头上的疼。天不亮就得喂牛、挑水,镰刀割破手也不敢吭声,稍有差池就挨皮鞭。最饿的时候,他啃过树皮、嚼过观音土,有次偷摸藏了半块红薯,被发现后遭毒打,罚跪在院里的碎石子上,直到天亮。13岁那年,他趁着夜色逃了出来,光着脚跑了几十里路,一路打听着摸到大冶乡——听说没子嗣的大爷王忠义住在这儿。大爷见他浑身是伤、瘦得像根柴禾,抱着他落了泪:“保才,跟我过吧,以后我养你。”就这样,他过继给大爷,在吴庄村落了脚。大爷虽不富裕,却总把窝头掰给他大半,还送他去夜校。夜校的油灯昏昏黄黄,他盯着黑板上的字,像盯着救命的稻草,四爷偶尔来看他,摸着他的头说:“认字才能不受欺负,咱穷人要想抬头,得先识文断字。”
有天夜里,四爷悄悄塞给他一本油印小册子,封面上“共产党”三个字烫得人心慌。“这是能让天下穷娃子有书读的队伍。”四爷的声音压得很低,眼里却闪着光。王保才把册子藏在炕洞里,夜里就着月光偷偷看,那些“打土豪、分田地”的字,像种子落进了心里。
1950年,村里要选年轻人去登封师范学教书,干部想起了这个总在夜校待到最晚的娃。大爷翻箱倒柜找出攒了半年的一块银元,塞给他说:“去吧,当老师,教咱村娃认字,比啥都强。”他背着大爷连夜缝的布包,包里揣着硬邦邦的窝头,走在去县城的路上,脚踩在黄土路上,一步比一步沉——他知道,这是要去圆一个梦,一个让更多像他一样的穷孩子能安稳读书的梦。

讲台:田埂印足迹,粉笔写春秋
1951年的春天,王保才第一次站在王村乡小学的讲台前。土坯垒的黑板,学生自带的板凳,三十多个娃瞪着眼睛看他,像一群等着喂食的小鸟。他攥着课本的手直冒汗,却清晰地说出第一句话:“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最实在的理——就像咱种地,撒下种子才长庄稼。”
他教语文,会把课文编成顺口溜;教历史,就带学生去村头看老槐树,说“这树见过光绪年间的事”。有个放羊娃总逃课,他就跟着去山坡,坐在石头上跟娃说:“你看远处的山,翻过才有新景致;念书也一样,认的字多了,路才宽。”后来那娃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初中的。
1953年,他被推荐去开封师范深造。第一次坐火车,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城市的高楼掠过,心里念叨:“啥时候咱农村娃也能在这样的教室里上课?”两年里,他的笔记记了满满三木箱,数学公式抄在烟盒上,教育学理论译成家乡话,回来时箱子太沉,他就背着走,累了就坐在路边啃干粮,心里却甜得很。
1956年入党那天,他对着党旗宣誓,声音响得很。同年当王村学校教导副主任,他定了条规矩:教案必须手写,连标点都不能错。有老师图省事,他就陪着重写,一边改一边说:“咱笔下的字,将来都是娃们脚下的路,半点马虎不得。”他的备课本上,红笔圈点密密麻麻,比学生的作业还认真。
1964年调去沁水小学当校长,那地方更偏,教室漏风,学生冬天上课哈着白气。他带着老师糊窗户、垫地基,在操场边开了两亩菜地,说“种菜换钱,给娃们买纸笔”。有次暴雨冲垮了教室后墙,他光着膀子带头搬石头,泥浆溅满脸,笑着说:“这墙得垒结实,要让娃们坐得安稳。”在沁水的6年,这所“三类校”的升学率翻了两番,家长们提着鸡蛋来谢,他愣是让拎回去:“娃出息了,比啥都强。”
1970年去弋湾时,他已经是7个娃的爹。家到学校5里地,他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布鞋磨穿了就垫干草,雨天摔进泥坑爬起来继续走,裤脚永远沾着黄泥巴。有老师劝他买自行车,他摆手:“走路能琢磨事——昨天那道几何题,我又想了个土法子。”
弋湾小学后来改成中学,他成了第一任校长。土坯房当教室,墨汁刷的黑板,他却在第一次会上说:“条件差咱认,但教不好书,对不起送娃来的爹妈!”他教政治课,把报纸剪下来贴成“土教材”,用“四个现代化就是顿顿吃白面”这样的大白话,让农村娃懂了大道理。每天早读前,雷打不动讲十分钟时事,哪怕咳得直不起腰,也会提前写好板书:“老师不上课,跟农民不种地一个理——误了时节,啥都收不成。”
中心校总“掐尖”,把尖子生抽走,他偏不信邪。每天放学后,毕业班多补一小时;周末把差生叫到学校,他亲自守着做题。有年中考前,数学成了短板,他连着半个月泡在教室,晚上给学生讲题,谁困了塞块硬糖,自己喝最便宜的茶叶水提神。那年中考,弋湾中学数学平均分在开封地区排第三,比中心校还高5分。红榜贴出来那天,他站在榜前抹泪,那泪滴在黄土地上,像撒下了一颗种子。
直到1994年退休,他在弋湾站了24年讲台。有人算过,他走的田埂路能绕登封两圈,批改的作业能堆满半间教室,送走的学生里,光中专生就有一百多个。

校魂:严字刻风骨,暖语润人心
王保才的“严”,在弋湾是出了名的。有年轻老师讲错“鸦片战争”的年份,他没当众批评,下课后拉到槐树下,掏出标着三个红圈的备课本:“你看,这页我标了红圈,就是怕记错。教历史不能马虎,错一个字,可能误孩子一辈子。”
他抓教学“准得很”。每学期开学,必组织老师逐字逐句抠大纲,从教材选用到课堂纪律,条条框框写得明明白白。谁的课上学生走神多了,他搬个板凳听课,课后盯着改教案:“不是娃不听,是你没讲进他们心里。”有个刚分配的老师让学生自习代替讲课,他陪着重备三天课,直到对方把每个知识点、互动环节都想透才罢休。
但这份严,裹着化不开的暖。1983年冬天,他的学生景中朝师范毕业刚到弋湾任教,被安排在校长办公室暂住。夜里铺开铺盖,才发现王保才的三闺女在角落搭了张小铁床——她在学校读初中,没宿舍,就住这儿。景中朝正尴尬,王保才已拉着女儿往外走:“跟同学挤挤,让老师住踏实。”后来他才知,校长女儿和三个女生挤一张床,冻醒了就裹着棉袄坐天亮,却从没抱怨过。
董增寿老师的女儿急病住院,300块住院费难住了一家人。那会儿老师月工资才几十块,王保才听说了,揣着个布包找上门。布包里有给七个孩子交学费的毛票、攒着买煤的钱,凑够300块塞过去:“先治病,钱的事往后搁。”董增寿红着眼要写借条,他按住说:“同事就是兄弟,见难不帮,愧当党员。”
为让家远的老师不啃干馍,他开了教师食堂。粮食从让大家从自家带,菜让家属轮流带,谁不好意思来,他就端着碗往人办公室送:“吃饱了才有力气教娃!”有个女老师生了孩子,他让食堂每天炖鸡汤,发动女同事轮流照看,说“咱校的人,就得互相帮衬着过”。

品骨:清风荡浊气,合力聚心魂
在弋湾中学,老师们常说:“王校长眼里,只有‘对不对’,没有‘亲不亲’。”他从不搞“办公室政治”,评优秀教师时,标准列得清清楚楚:教学成绩、学生评价、创新方法,条条量化,谁也钻不了空子。
有年,一位跟他相熟的老师差了几分,找他说情。他翻出评分表,指着“作业批改粗糙”的评语说:“改了这些,下次准能评上。”最后把荣誉给了年轻的景中朝,只因为“他备课到深夜的次数,全校最多”。
对待学生,他更是一碗水端平。穷人家的娃没铅笔,他从家里带来一捆;富户的孩子调皮,该批评照样批评。有个村干部的儿子逃课,家长来说情:“娃还小。”他怼回去:“正因为小,才得教他走正道——你当干部的,更该懂这理。”后来那孩子被他盯着补课,考上了县一中,家长提着鸡蛋来谢,他硬是让拎回去:“娃出息了,比啥都强。”
他最厉害的本事,是“把一群人拧成一股绳”。同事说:“他不用喊口号,自己先干在前头。”备考时,他跟老师一起熬夜;修教室时,他扛着锄头先上;有老师家收麦子,他带着没课的老师去帮忙。在他带动下,弋湾中学“教风正、学风正”,哪怕生源被“掐尖”,成绩照样甩中心校一截。有年中心校想挖走他们的数学组长,那老师说:“王校长待咱如家人,给座金山也不挪窝。”

远识:育师成栋梁,薪火代代传
王保才常说:“老师是树,根扎得深,才能给娃们遮荫。”他比谁都清楚,乡村学校留不住老师,一切都是空谈。为了让弋湾中学有支稳得住、能打仗的教师队伍,他成了最“爱跑腿”的校长——带着炒花生、红薯干,一趟趟往周边乡镇跑,去挖那些教学厉害的骨干教师。“咱校虽偏,但人心热。”他拉着外校老师的手掏心窝子,“来了我给你搭伙,住的地方我去跟村民借,保准让你安安心心教书。”有老师家远,他挨家挨户找村民商量,把闲置的厢房收拾出来当宿舍,还在办公室支起木板床,自己的办公桌上常年堆着老师的行李。
更难得的是,他总记着那些从弋湾走出去的师范生。每年师范院校放暑假,他都带着糖果去家访,坐在炕沿上跟学生说:“学校盼着你们回来,娃们等着你们教。”一来二去,先后有10多个本校毕业的师范生回了乡,成了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的顶梁柱。他们说:“王校长当年教咱‘滴水之恩当涌泉报’,现在就是咱报恩的时候。”
每周三晚上的集体备课,是弋湾雷打不动的“充电时间”。煤油灯底下,他带着老师围坐成圈,年轻的讲新教法,年老的传老经验,吵吵嚷嚷却满是干货。讲《孔乙己》时,他突然起身:“咱村老秀才爱赊酒,跟课文里一个样,明天带你们去唠唠。”把书本里的字变成村口的人,学生们听得眼睛发亮。他还逼着出去进修的老师开“取经会”,景中朝从开封学了数学新法,被他追着讲了三晚,直到每个老师都学会才罢休。
这份对教育的执着,早已融进了家风里。他的“教学管理日记”记了五十多年,泛黄的纸页上写着“要想生活好,必须有文化”“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成了王家四代人续写不息的传家宝。他常对子女说:“读书不是为了跳出去,是为了回来把根扎得更深。”在他的影响下,家里先后有多人走上讲台,而这个58口人的大家庭里,28名共产党员像星星一样散在各行各业,“全国五好家庭”“全国文明家庭”的牌匾,在堂屋里闪着光——那是比任何奖状都珍贵的勋章。

余晖:退而志未休,清风传久长
时光悠悠,岁月匆匆,王保才校长虽已离去,但他的精神却如沁水村那棵老槐树,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枝繁叶茂,荫庇后人。
2024年9月的那场座谈会,是对他一生功绩的回望,更是对其精神传承的期许。会上,众人的讲述仿佛一幅幅鲜活的画卷,将王保才校长的往昔岁月一一展现。他四十年如一日,手持粉笔,耕耘于教育沃土,用知识与爱心浇灌着祖国的花朵;退休后,又以锄头为笔,公章为印,在乡村治理的画卷上继续挥毫泼墨,书写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担当。
他的日记,承载着一生的智慧与情怀,如今已成为家族的瑰宝,被后代们续写传承,那字里行间的教诲,如明灯照亮着子孙前行的道路。村里学校中,那悠扬的劝学歌,依旧声声传唱,似在诉说着他对求知学子的殷切期望。而他所倡导的文明风尚、所制定的村规民约,早已融入沁水村的血脉,成为乡村发展的精神基石。
王保才校长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沁水村的过去,也指引着它的未来。他的清风正气,他的奉献精神,已深深烙印在每一个沁水人的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奋发图强,鼓舞着一批又一批的村民建设家园。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沁水村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位曾为教育事业耗尽心血、为乡村发展鞠躬尽瘁的老人。他的故事,将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成为永恒的传奇。而他所播下的希望种子,也将在岁月的滋养下,不断茁壮成长,绽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让沁水村的明天,如那绚烂余晖,虽近黄昏,却依然光芒万丈,温暖而悠长。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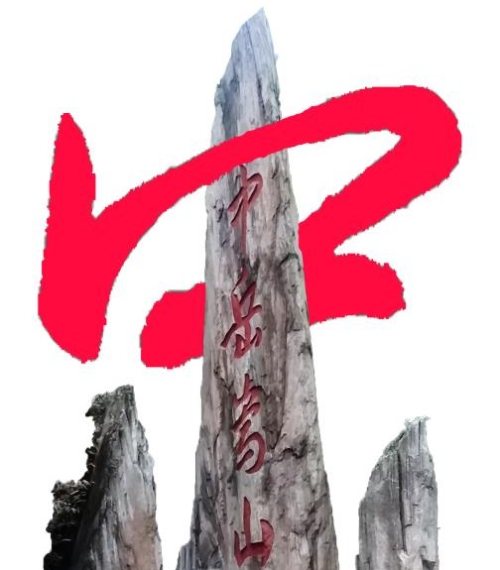 正观登封
正观登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