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牟新区(县)弘毅高中 李志霞
上周未我到中牟县官渡博物馆参观,印象特别深的器物是石磨盘和石磨棒。乍一看,它很像家里的案板和擀面杖。但又不是,既熟悉又陌生。听了讲解后,才知道这是远古时代的农具,用于谷物的研磨和去壳。
石磨盘的形状是一块长石板,两头呈圆弧形。像一片碾扁的大块面坯,它是用整块的砂岩石磨制而成的。石磨棒近乎圆柱体,中间略细,两端略粗,大概是碾磨日久所致。
经过深入了解,才知道这是裴李岗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它们已经穿越了八干年的历史长河,见证着古老的的农耕文化,见证着当年农业生产的发达,见证着几千年前中原地区人们的智慧。从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转变,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推进,这些器物的发明,使种植的作物向多样化发展。
苏子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一个人短短几十年的光阴于历史的长河中,渺小得微不足道,但是人类的智慧之光却可以汇成星河万里,璀璨夺目。每一个器物的发明,都推动了社会的进展,绽放着人类智慧的火花。从石磨盘我想到了我记忆中的农耕生活。
从我有记忆起,我的家乡种植的谷物就是小麦。小麦在全世界的种植史已有一万多年,但在中国其实只有三千多年。主要是石磨的发明使得小麦的种植得以大面积推广。唐代白居易在《观刈麦》一诗中用白描手法描绘了收麦子时的场景:“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小满一过,一望无际的麦田里,麦浪滚滚,像一片金灿灿的海洋,承载着农人沉甸甸的希望。
在没有自动收割机的年代,收麦子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又被称作虎口夺粮,只有全家齐上阵才能尽快做到颗粒归仓,在外地打工的劳动力无论再忙都要回家收麦子。收割、脱粒、扬场、晾晒、储存,工序复杂,每个工序都不简单,特别耗费体力,尤其离不开男壮力。从我有记忆起,在麦收时节,大人都是白天收割,顶着烈日的酷晒,忍受着麦芒的刺痛,腰弯成九十度,挥舞着镰刀,重复着单调的动作,手都能磨出茧,甚至会扎出血。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去地里用架子车把麦子运到场里面,之所以赶大早拉,是因为早上有露水,麦子略湿润,好装,中午太干燥,没法装。运载的时候为了多装点,都要尽可能压得瓷实一点,有小孩子在上面压着车会好装很多。我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压车,如果不压着麦秸秆特别光滑,很不好装。每一车都想尽可能地多装些,直到装得不能再装时,爸爸妈妈就用绳子捆上,我在上面紧紧拽着绳子,爸爸拉着车,妈妈推着,缓缓地走出麦田,再拉到场里面。
时不时地会有麦穗往下掉,因为拉麦子的车比较多,路上零零碎碎掉下的麦穗也不少,特别是田地里更多些,如果有闲专门拾穗的话,一个农忙都能拾不少麦穗。在上初中时,我看到过法国画家米勒的一幅名为《拾穗者》的油画,背景是广袤无垠的麦田,还有几个高高的麦秸垛。几个农村打扮的妇女,在弯腰拣拾麦穗。艺术无国界,这幅油画曾经令年少的我很是神往。在那个信息很不发达的时代,我们只有通过图画和文字才能非常直观地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在遥远的国度和遥远的年代,居然也有很多人在从事着我们所熟悉的劳动,诠释着什么是“粒粒皆辛苦”。
麦子拉到场里面之后,要用牛拉的大石滚碾场,碾完之后扬场也是非常辛苦的活。扬场要有适度的风,太大了会刮跑,太小了扬不起来。要迎着风扬,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用木掀扬,另一个用大扫帚扫碎麦秸秆和麦糠。儿时的打麦场,是大人的繁忙场,也是孩子们的欢乐场。孩子们在麦秸堆里打滚儿,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
再后来,由人工割麦变为半机械化收割,再后来到全机械化收麦,直接在地里颗粒归仓,麦秸秆还田。机器轰鸣取代了牛马嘶鸣。
近些年乡村拆迁,我的老家已经没有土地了,但是每每有时间的时候,我还是特别喜欢到麦田里转转,觉得那是最美的风景,能唤起我很多儿时的回忆。父母更是难以忘怀那些劳作的时光。有很多细节我的记忆已经模糊,是听妈妈清晰的叙述才得以完成这篇文章。
小麦,承载着一代又代农民刻骨铭心的记忆。麦香,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故乡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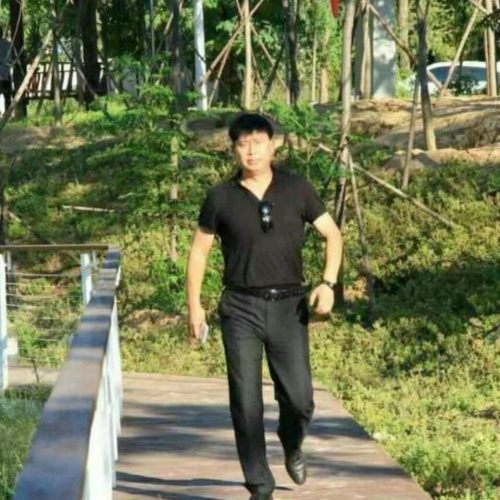
中牟恋歌
冷暖自知,友谊长存!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