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街开业后,这巴掌大的街巷竟一时涌出四五家围炉煮茶的小店。
衣着时髦的年轻人,室内,墙角,树下,围炉而坐,眉目爽朗,在手机上分享着标配的精致生活。
这是怎样一个时代,亦真亦假,信息的移动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移动。
人们沉浸在虚拟的幸福里,没有人怀疑千篇一律的情感和悲欢。
如果有一天身体也可以分解为数字,可以以波的形式移动,我们是否可以走出银河系?
那里是什么样的风景,是不是也有华山路,也有梧桐树和雪后晴朗的冬天?
我们可以坐在银河的边缘喝茶,看一看四维时空里的情爱。

茶壶里也是普洱吧,要么就是白茶,加一颗烧焦的红枣进去,香甜的气息就在茶桌上弥漫。
除了红枣,炉网上一定还烤着花生、桂圆、核桃、红薯和桔子。
烤热的桔子去了酸,像热果冻,入口化作一团温润。
低温的环境,实在值得这一盏炉火,可惜还是太小了,远不如从前家里的火炉。
那时的冬天,火炉是家家户户的中心。大人小孩都围在火炉边,烧水、烤花生、说笑。
偶尔散场前还会煮一锅热汤面,捧着瓷碗吃完心满意足地回屋睡觉。
汤面做得好不好,我爷爷的说法叫“融”。“融”,就是好,就是功夫到了,各种食材煮的火候都到了,融合的恰到好处,喝着顺溜了、润滑了、舒服了。
那就叫“融”。
那种粗粝的幸福感,如今已经全面升级了。
茶要老,陈皮要老,白铁皮水壶换成了黑铸铁壶,自来水换成了瓶装水,搪瓷大茶缸换成了各式小茶盏。
吉州窑的木叶盏,耀州窑的斗笠盏,建州窑的鹧鸪斑,钧窑看走泥纹,汝窑看芝麻钉。
我最喜欢的是斗笠盏,只是喜欢,说不出原因,最不理解的,是建盏。
又黑,又粗,又大,人们喜欢它什么呢?拿着喝茶不觉得笨重吗?直到看了审美狂人徽宗皇帝的《大观茶论》,才明白建盏的用处。
宋朝斗茶盛行,斗茶不是煮茶,也不冲泡,而是点茶。
用徽宗的说法是“碎玉锵金,啜英咀华……环注盏畔,渐加周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疏星皎月,灿然而生……乳雾汹涌,溢盏而起,沫轻如花,饽厚如雪……和美具足,馨香四达……”
原来我们喝茶是要拉花的!现代人喝咖啡拉花弄出一个心形弱爆了,我们用茶粉就生打出花来,而且是乳雾汹涌,溢盏而起!
因“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所以“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
这便是宋朝流行建盏的原因了,器型大利于击拂,胎厚利于保温,色黑方可衬托乳白。
喝茶,不仅是味觉的满足,更是视觉的愉悦,不仅是物质的享受,更是精神的升华!

这极致的追求,民间自然是望尘莫及,更不要说赓续流传了。
我们看大画家苏汉臣的《卖浆图》,我总觉得那就是宋代民间的点茶,既迎合了上流社会的趣味,又化繁为简、老少咸宜。
既有形而上的极致之美,又有形而下的热气腾腾,这就是我们曾经拥有的生活。
我们可以品味徽宗皇帝的“中澹闲洁,韵高致静”,也可以像词人戴复古那样“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
转眼又到岁尾。
转眼千年已过。
2023年12月22日,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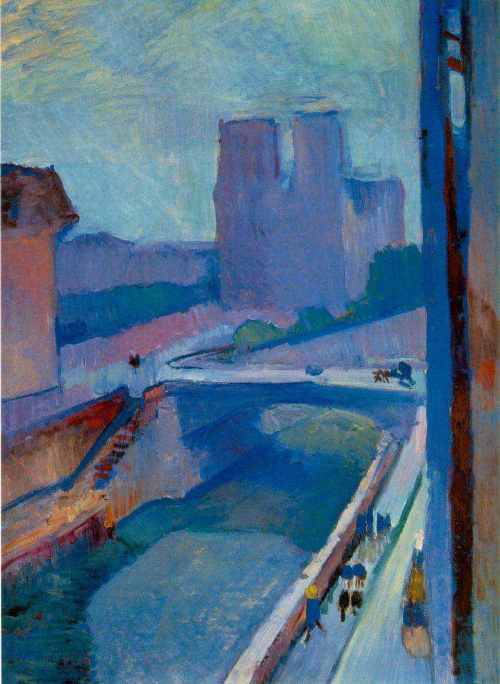
张新彬
张新彬正观号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