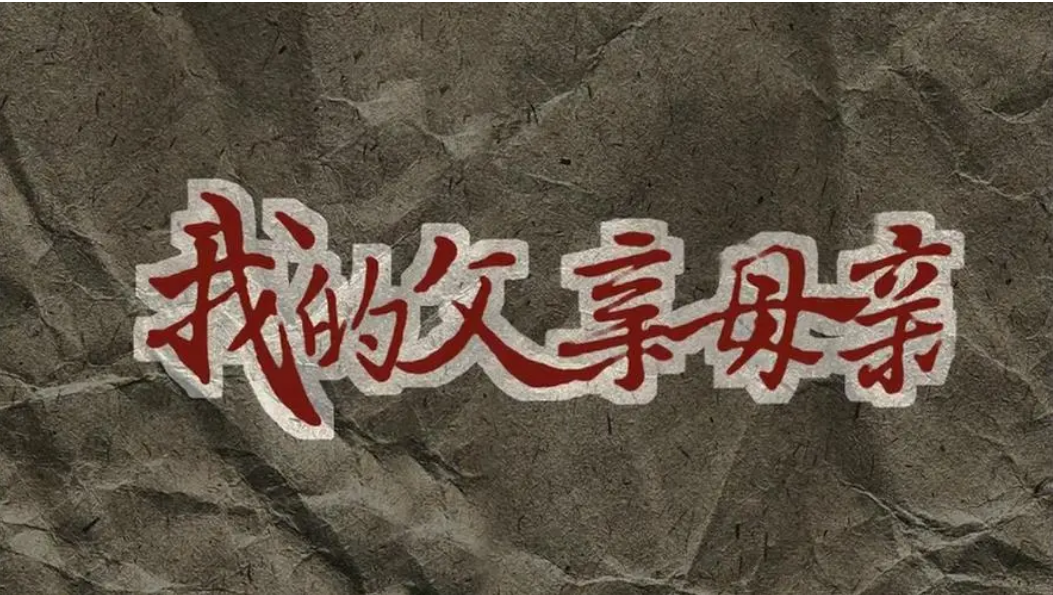
第十二集我的父亲母亲
母亲跨入我们刘氏家门时,家徒四壁,缺衣少穿,就连做饭的锅,也是漏了好几个洞,每到烧火前,需要先用一丁点面糊把窟窿眼儿糊住。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日子一天天凑合着过。好在母亲的到来给家里增添了壮劳力,“工分儿”比以前挣得多了,生活上要比以前略好一些,家的氛围也鲜活了许多。
然而一年之后,更艰难的岁月到来了。这种艰难,在全国层面表现为学校停办、教师成了“臭老九”,医院受冲击,名医被打成“右派”,大批专家学者被批斗致死。这种艰难,对我家而言,不是物质上的短缺,而是精神层面的折磨。1966年“文革”开始后,由流氓无产者任骨干的“造反派”组成村“革命委员会”,对成分不好的家庭捏造证据,罗织罪名,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人身攻击。我家成了村“革委会”攻击的重点——本来就是“富农”后代,又娶了“国民党反动派眷属”为妻,这还了得。父亲几乎天天挨批斗、写检查,而且,生产队里诸如掏大粪、背麻袋之类的苦活儿、重活儿、脏活儿、累活儿,全推给我父亲去干。亏得我父亲从小练就一身好功夫,再苦再累,父亲都咬牙坚持,没有倒下。

这种非人的待遇一直持续了十年……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很多人被批斗致死,很多家庭夫妻反目、妻离子散,而母亲始终陪在父亲身边,相濡以沫,共度时艰。那些年给我家帮助特别大的,要数我姨。母亲出嫁后,我姨回家务农陪着姥姥过日子。姨父王照义在邮电部第四工程公司(郑州)工作,条件要好很多。每次从郑州回来,和蔼可亲的姨父都约我们全家去石营村姥姥家打牙祭,我们返回时每个人肩上都要扛很多东西,给苦难主题的乐章送来一些跳跃的音符。
1976年10月,普天欢唱《祝酒歌》,一个磨难时代结束了。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为了解决人才断层问题,国家迫不及待从时间上打破招生常规,当年12月恢复高考。这件事如同一声春雷,随后,全国各地高中、初中雨后春笋般建立或恢复办学。根据上级部署,我的家乡前营和邻村后营也联合办了一所初中,但急缺师资。这个时候,村干部破天荒踏进了我家的门,以高“工分儿”的待遇劝我父亲从教当老师。这里要感谢一个人,父亲的二姨父、村里前街的杨侠普。解放前他家虽穷,但人好,奶奶毅然将二妹许他为妻。后来划成分,他家因穷受益,杨侠普不仅入了党,后来还当了村干部,没少为我家帮忙。
被春雷惊起的,还有医疗卫生事业。1978年春,万古镇卫生院的院长也多次邀请我的父亲前往坐诊执业。
面对突如其来的喜事,父亲陷入了思索,按说,作为中医世家的传承人,坐堂行医方为正途,然而又眼馋当老师的高“工分儿”待遇。母亲的一席话,使我的父亲心中豁然开朗——咱就当老师,在乎的不是高“工分儿”待遇,而是从长远考虑,可以给三个儿子提供无限的文化学习空间;况且,既有一身医术,谁也剥夺不走,当老师的同时,也永远是一名医生。
就这样,从1978年开始,父亲成了一名民办教师,教学之余辅导我们弟兄三个学习。母亲则在家务农,供养全家人的吃穿用度。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寒江独钓
寒江独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