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界》封面
1931年3月,上海诞生了一份面向全国青年读者的综合性刊物。虽曰“综合性”,其实新文学占有相当的比例和突出的位置,水准并不亚于当时那些新文学名刊。而且,该刊出版时间前后长达十一年之久,共出八十六期(其间因全面抗战爆发而被迫停刊八年又四个月),版式也从最初的32开横排本改到16开竖排本再到复刊后的32开竖排本。这在1930至1940年代出版的刊物中是颇为少见的。这份刊物就是上海北新书局的《青年界》月刊。
《青年界》封面
要讨论《青年界》的历史功绩,还得从出版《青年界》的北新书局说起。李小峰主持的北新书局1924年5月创办于北京①,以出版周氏兄弟、郁达夫、冰心等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而驰名文坛。1926年6月,北新书局在上海设立分局,同年8月《北新》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可视为北新书局南下上海的先声。北新书局编辑部全体迁移到沪,则在1927年9月之前②。1927年11月,原由北京北新书局发行的《语丝》周刊第155和156期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自12月17日第4卷第1期起,《语丝》改由鲁迅、柔石先后编辑。这样,就形成了上海北新书局同时出版《语丝》和《北新》两大新文学杂志的新局面。这在1920年代末的新文学刊物出版中是很少见的,可见北新书局当时的出版雄心。

北新书局发行的新文学期刊
然而,到了1930年3月,已改由李小峰主编的《语丝》在出版了第5卷第52期后停刊;同年12月,《北新》出版了第4卷第23、24期合刊后停刊。同年7月才创刊的由赵景深主编、北新印行的《现代文学》月刊也在12月出版了第6期后停刊。《语丝》《北新》和《现代文学》先后停刊的具体原因,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但北新书局试图重新整合刊物出版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三个月后,随着《青年界》的问世,北新出版新文学刊物的“空窗期”结束了。
当时,上海滩上除了开明书店已在出版夏丏尊、叶圣陶等先后主编的《中学生》,还没有一种面向更广大的青年读者的综合性刊物,而《青年界》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青年界》创刊号的《编辑者言》中就这样开宗明义:
由此可见,《青年界》出版宗旨是为当时“一般青年”提供“精神的食料”。当然,在多种多样的“精神食料”中,文学历来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青年界》侧重新文学创作和评论,以及外国文学译介,也就顺理成章。正如《编辑者言》中“具体地说一说”的几条里,第一条就是“为增进读者对于国外作家之认识起见,特设‘作家介绍’一栏,每期介绍一人”;而第五条又强调“久已广告而终未与读者相见的长篇小说《蜃楼》,从本期起,按期发表。堪慰郁(达夫)先生的爱读者之渴望。”
对于综合性的《青年界》的创刊,编者之一的赵景深在1946年1月《青年界》新1卷第1号的《复刊词》里又是这样回忆的:
从中可知,《青年界》最初的编辑是石民,创刊号的《编辑者言》很可能出自石民手笔。由于出版时间很长,《青年界》可以分为前后期,1931—1937年为前期,1946—1949年为后期。因此,《青年界》编辑部人员也多次调整。其中与力最大者,莫过于李小峰、石民和赵景深,先后参与其事的还有袁嘉华、姜亮夫、杨晋豪、厉厂樵等③,他们中大都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或学者。我们今天回顾《青年界》的历程时,不应遗忘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当年为办好《青年界》所做出的努力。
《青年界》既然定位于“不限于一种”精神食料的“杂”之又杂的综合性杂志,当然在内容上也有相应的精心设计。从创刊号开始,《青年界》就设置了许多定期或不定期或不断有所更替的专栏,其中有“社谈”“给青年”“一般讲话”“时事讲话”“国际问题讲话”“社会科学讲话”“新闻讲话”“自然科学讲话”“科学新谈”“常识讲话”“医学讲话”“新术语解释”,以及“论文”“学术讲话”“国文讲话”“艺术讲话”“电影栏”“英文讲话”等等,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延请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为之撰稿。当然,《青年界》既以新文学为重要指归,关于新文学方面的专栏设置同样精心安排,包括了“创作小说”“小品”“随笔”“诗选”“书评”“作家介绍”“文坛消息”“海外通信”“青年文艺”,以及古典文学方面的“杂纂”和综合的“青年论坛”等等,应有尽有。
不妨以1931年3月出版的《青年界》创刊号为例略做考察。创刊号发表了岂明(周作人)的小品《草木虫鱼》、郑振铎的《罗贯中》、郁达夫的连载小说《蜃楼》(一至六) 和书评《读刘大杰著的〈昨日之花〉》、郢生(叶圣陶)的童话《绝了种的人》、许钦文的短篇《新同学》、白薇的短篇《一个台湾女子的谈话》、徐霞村的新诗《给——》、杨骚的新诗《临终》,刘大杰的《刘易士小论》和钱歌川翻译的刘易士短篇《马车夫》等,还有梁遇春、谢六逸、石民的翻译作品。除了新文学创作、评论和翻译,创刊号还刊出了倪贻德的《近代绘画代表作》、杨东莼的《一九三〇年国际情势概况》、漆琪生的《世界列强市场争夺战之近况及与我国之关系》等。自然也有直接面向青年读者的杨人楩的《现在青年的苦闷》、衣萍的《青年应该读什么书》等。创刊号内容之丰富多彩,就是将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值得称道的。
由此可见,《青年界》作者阵容十分强大,至少从新文学这个方面来说是如此的。五四以降的新文学名家,从周氏兄弟和胡适开始,相当部分是前期《青年界》的作者,人数之多出乎我们的想象。试看如下这个骄人的作者名单: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冰心、王统照、鲁彦、田汉、洪深、胡山源、汪静之、朱湘、许钦文、许杰、凌叔华、苏雪林、废名、于赓虞、罗念生、钱歌川、阿英、老舍、沈从文、黎锦明、白薇④、谢冰莹、叶灵凤、叶鼎洛、梁遇春、张天翼、穆时英、戴望舒、施蛰存、李健吾、曹聚仁、臧克家、艾芜、李长之……这个名单还可开列很长很长。这些作者发表在《青年界》上的作品,许多都是鲜为人知的集外文。在前期《青年界》上,周作人发表的作品有《金枝上的叶子》《塞耳彭自然史》《自己的文章》等24篇之多,郁达夫则有《学生运动在中国》《批评的态度》《文艺与道德》等12篇,就影响力而言,他们两位可视为前期《青年界》的台柱。而即便只发表过一篇作品的,也有不能不提和值得注意的,如胡风在1936年1月第9卷第1号发表的《教支那话的支那人》和巴金在1937年1月第11卷第1号发表的《关于〈春〉》。到了《青年界》后期,除了前期作者中不少位继续为之撰稿,又新增了丰子恺、陈翔鹤、朱维基、于伶、陈灵犀、吕白华、赵清阁、罗玉君、田禽、刘北汜、欧阳翠等新老名家。当然,这个名单仍举不胜举。
在《青年界》作者群中,鲁迅是值得特别说一说的。《青年界》创刊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未曾为之写过一篇稿。众所周知,自小说集《呐喊》《彷徨》起,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集都在北新书局出版,鲁迅也经常为《语丝》《北新》 撰稿,以鲁迅与北新书局这么密切的关系,这是出人意料的,却并非无迹可寻。1929年8月,因为北新多次拖欠鲁迅版税,鲁迅欲诉之法律,幸而有郁达夫等从中调解,此事才得以妥善解决。但双方的芥蒂并未完全消除。此后《青年界》出刊,鲁迅未为之撰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尽管鲁迅与《青年界》首任编辑石民私交并不错。同时,也不排除另一层含义,当时官方的文网已越来越严酷,鲁迅不为《青年界》撰文,或也有为北新着想的用意在。
机会终于来了,虽然是由刘半农的英年早逝引起。1934年7月14日,鲁迅《新青年》时期的“老朋友”刘半农因在绥远一带考察方言时染病,逝世于北平。噩耗传出,全国文化界悲悼。《青年界》即着手组织纪念专辑,李小峰理所当然地想到了鲁迅。同年7月31日鲁迅日记云:“午后得李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⑤应是李小峰向鲁迅邀稿,鲁迅当天就作复:“关于半农,我可以写几句,不过不见得是好话,但也未必是坏话。”⑥这就是鲁迅名文《忆刘半农君》的由来。此文落款“八月一日”,可知鲁迅真的是有话要说,一天就一气呵成。鲁迅在文中深情回忆了与刘半农交往的始末,有赞扬有批评,特别强调:“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道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⑦8月12日,鲁迅把此文寄给李小峰时又说:“关于半农的文章,写了这一点,今呈上。作者的署名,现在很有些人要求我用旧笔名,或者是没有什么大关系了。但我不明白底细,请兄酌定。改用唐俟亦可。”⑧鲁迅的考虑是很周到的。《忆刘半农君》在1934年10月《青年界》第6卷第3号刊出时,署名是“鲁迅”,这也是鲁迅的名字首次出现在《青年界》。
到了1936年2月,鲁迅的名字再次出现于《青年界》,而这次又是北新书局主动约稿。1935年12月21日鲁迅日记云:“得赵景深信。得小峰信……”⑨当时赵景深正是《青年界》的编辑。显然,《青年界》为1936年新年号,致信鲁迅请其撰稿。鲁迅12月23日日记云:“复小峰信,附与赵景深笺,并稿一。”⑩正是寄给《青年界》新稿《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系鲁迅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而作,原文日文,鲁迅亲自译为中文。但鲁迅在致赵景深信中明确提出“畏与天下文坛闻人,一同在第一期上耀武扬威也”⑪,故此文刊于是年2月《青年界》第9卷第2号,可见鲁迅对《青年界》一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仍不无保留。这是鲁迅生前与《青年界》的两次成功的合作,是必须提到的。
鲁迅逝世后,鲁迅的作品又先后两次出现在《青年界》上。第一次是《青年界》1937年6月第12卷第1号推出的“日记特辑”,许广平提供了鲁迅1936年10月10日和11日两天日记。这是鲁迅逝世前不久的日记,也是鲁迅日记在他逝世之后首次公布于世,11日的日记明确地记载“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足以证明鲁迅逝世前已在考虑迁居这件大事。第二次是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新6卷第4号和第5号,也即《青年界》的最后两期,又连载了《鲁迅书简补遗——给李小峰的三十六封信》。这篇长文又一次提供了研究鲁迅、研究鲁迅与北新书局关系的第一手史料,这也是不可不注意到的。
由此,又应该提到《青年界》另一个显著且卓有成效的特色,那就是不断地推出特辑。特辑又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纪念已逝作家的特辑,第二类是某个专题的特辑。先说第一类。《青年界》1934年2月第5卷第2号是“朱湘纪念专号”,用接近整期的篇幅沉痛哀悼英年早逝的诗人朱湘。“专号”分“朱湘纪念”和“朱湘遗著”两大部分。纪念部分刊出了苏雪林的《论朱湘的诗》、柳无忌的《我所认识的子源》、顾凤城的《忆朱湘》和何德明、吕绍光的同题诗《悼朱湘》等,以及郑振铎、闻一多、饶孟侃、柳无忌、黄翼、苏雪林等“哀悼朱湘的信”,还有赵景深的《朱湘著译编目》。而遗著部分,也刊出了朱湘的回忆录《我的新文学生活》、评论《诗的用字》、散文《江行的晨暮》《投考》《说诙谐》等,译文《索赫拉与鲁斯通》(英国安诺德作),以及“遗书摘选”等。朱湘1933年12月5日投长江自尽,两个月后,《青年界》的这个纪念专号就面世了,不仅是当时文学杂志中悼念朱湘内容最为全面丰赡的一个纪念专号,至今仍不失为研究朱湘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十分难得。
上述鲁迅的《忆刘半农君》其实也是为1934年7月《青年界》第6卷第3号的“刘复先生纪念”特辑而作的。这个特辑还收入了蔡元培的《刘半农先生不死》、全增嘏的《刘复博士》、徐霞村的《半农先生和我》、姜亮夫的《介绍〈四声实验录〉》和赵景深的《刘复的〈中国文法讲话〉》,同样纪念性和学术性兼具,颇为人醒目。到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溘然长逝。《青年界》同人震惊之余,理所当然地在同年11月第10卷第4号以头条的位置刊出“鲁迅先生逝世纪念”特辑,刊出了蔡元培的《鲁迅先生轶事》、许钦文的《鲁迅先生与新书业》和杨晋豪的《鲁迅先生》三篇纪念文。到了下一期即12月第10卷第5号再次刊出“鲁迅先生纪念”特辑,刊出黎锦明的《两次访钟楼记》、金性尧的《鲁迅先生的旧诗》和朱雯的《悼鲁迅先生》,而且,该期“社谈”栏中又发表了杨晋豪的《追忆送鲁迅先生的葬礼》,“青年文艺”栏中也发表了朱亚南的《悼鲁迅先生》、高华甫的《悼文坛巨星鲁迅》、邓丁的《广州鲁迅先生追悼会》、康国栋的《忆鲁迅》等文。《青年界》对鲁迅的悼念可说是隆重和持续的,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各种刊物中并不逊色。此外,《青年界》还刊登过“萧伯纳来华纪念”“屠格涅甫五十年死忌纪念”等特辑,均各具特色。

《青年界》“中国文学特辑”与“创作特辑”封面

《青年界》刊发的关于青年学习生活的特辑
后期《青年界》的特辑虽已不如前期那么周全,但仍有不少是专为青年读者而设的。1946年1月新第1卷第1号的“给青年特辑”、1947年3月、4月新第3卷第1号、第2号上的“推荐青年可读的书特辑”,都值得一提。特别是1948年9月、10月、11月新6卷第1号、第2号和第3号接连三期推出的“人物素描特辑”,除了追忆李叔同、鲁迅、徐悲鸿这样的大师,也写了普通人。如此集中地提供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颇有价值的回忆文字,真是可圈可点。当时人已在台湾的台静农的《许寿裳先生》一文,我就是在“人物素描特辑”(二)中发现的。
1930至194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主打新文学的综合性刊物中,《青年界》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是颇为显眼,广受赞誉的。当时就有读者这样评价《青年界》:“定价既廉, 内容又好,可以说是我们青年真正的最好读物。反过来说:也就是青年精神奋斗的场所。既能从内中得到他人的杰作,又可以在上边发表自己的思想,运用头脑,练习文章,于学识的裨益,诚非浅鲜!”⑭全面抗战爆发前,《青年界》发行全国,销量由“三千份逐渐发达到一万二千份”⑮,这可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抗战胜利复刊后,发行量虽然降至“两千份”,仍可维持,但出至1949年1月第6卷第5号,因“邮路不通,发行困难”⑯而被迫停刊。1949年6月,因上海已经解放,《青年界》提交“上海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申请登记书”筹备复刊,因与其他各种刊物一起均未获批准而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时光已经流逝了七十多年,当年深深吸引了众多青年读者的《青年界》,虽然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如有论者认为《青年界》对“五四启蒙的传承与转换”做出了贡献⑰,但与当年在上海出版的其他颇具影响的大型新文学刊物,如《小说月报》《新月》《现代》《文学》《论语》等相比,《青年界》的关注者和研究者毕竟不多。上海书店出版社这次影印全套《青年界》,以推动对《青年界》、对《青年界》与五四新文化传统、对《青年界》与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关系的研究,正其时也。

《青年界》(全24册)(民国期刊集成)
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后,曾有幸与《青年界》的两位编者,即赵景深先生和杨晋豪先生交往,得到过他们的指教,也曾听他们谈起过《青年界》。由于有这点因缘,在《青年界》影印本即将出版之际,不揣冒昧,大致梳理《青年界》的来龙去脉如上,供对《青年界》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2023年9月10日于上海梅川书舍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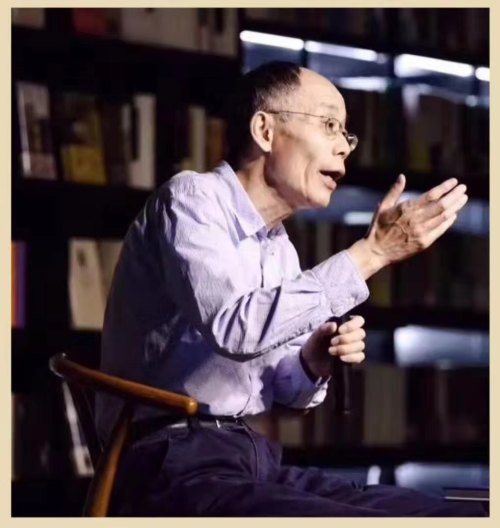
陈子善
陈子善官方正观号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