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六月,郑州雨水丰盈,宛若南方。
在雨中,二砂的草坪上,蚯蚓纷纷钻出泥土,引来了成群的乌鸦。
乌鸦大快朵颐,又衔了满嘴,飞回巢中育儿。
一种白眼圈儿的鸟也混迹其中,埋头寻觅,不知道叫什么。
宣传栏下,一对恋人依偎在一起,看着雨中的乌鸦。
一把黄色的雨伞,醒目地丢在一旁。
两个小孩呼叫着跑过,从马路上积水处踢起一片水花。
雨水丰润了泥土,除了蚯蚓和四处乱爬的蜗牛,爬叉也该蠢蠢欲动了吧。

晴日,终于开始像郑州的夏天,阳光充足、直接,尚未灼热。
一条火车虫从秦岭路边的花坛里爬出来,大摇大摆地开上了柏油路。
它的背部黑亮,两侧有金黄的花纹。
它的腿可真多,在路上笔直地前进,如果是觅食,那一定是搞错了方向。
它的腿可真短,怎么也跑不快。用手轻轻地按它,则迅速卷成一盘蚊香装死。
装了一会儿,似乎感觉问题不大,展开身体加速前进。
火车虫看起来是无害的,它交配的时候身体叠在一起,像开动的双层火车。

花坛里,松果菊像一朵朵降落伞。
它的头顶,人们精心种植的紫薇终于绽放了。
一簇簇淡紫色的小花拥在枝头,娇羞柔美、楚楚动人。
虽然看似柔弱,她却为郑州漫长的夏季顽强地延续着一抹彩色,一直到秋天。
她的身体光洁、敏感,轻轻地触摸就会微微颤动。
小时候,我们叫她“痒痒树”。
植物也是有触觉的。
含羞草感觉到触碰会迅速闭合,如果愣头愣脑的火车虫爬上了捕蝇草,那就是它的灭顶之灾。
好在,火车虫似乎总是在地面上活动。但是蚂蚁,就不一样了。
到处都是它。
地下,地上,花朵里,树叶上,雨中,太阳下……
它勤奋的身影,出现在所有的角落里。它们有着庞大的组织,分布式的决策,战斗不止的精神。
如果有一天,蚂蚁统治了世界,我一点也不会惊讶。
此刻,居然有一只爬上我的胳膊妄图吃我!太自不量力了吧。
典型的情况不明决心大,现在我还是老大,你们全家吃一辈子也吃不完啊。
我直接弹飞它,找路去吧你。
但是蚂蚁是不会迷路的,不管绕多大的圈子,它都能直线返回自己的家。
即便,它被弹到了一棵构树上。
啊!构树。

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苦寻不见,你看见了第一个,你发现俯拾皆是。
自从我看见了第一棵隐藏在小区角落里的构树后,神奇的规律再次出现了——
沿着秦岭路漫步,构树的身影依次浮现。
它们都在靠墙的角落里,趁着人类还没有动手,迅速长到了安全的高度。
真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树。
六月下旬,火红的构桃已经挂满了枝头,而它奇特的叶片上,一只漂亮的鹿蛾正准备产卵。
鹿蛾的美艳,有一丝凌厉,像不可触碰的警告。
鹿蛾的一生,只交配一次。
产卵,孵化,成长,结蛹,破茧,羽化,交配。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它静悄悄地进行着生命的循环。

天下万物,都在循环。
有的喧嚣,有的沉默。
草木、生灵、时间、空间,一切都会回到原点。
乌鸦瞪着眼睛大叫,孩子高呼着奔跑,火车鸣笛纵横,蚂蚁磨牙霍霍,鲤鱼搅动水声。
五叶藤紧紧地缠绕着被人们修剪成球形的冬青,在雨后的晴日,你惊讶地发现它已经成功将冬青覆盖。
山楂在孕育,柿子在孕育,石榴在孕育,核桃在孕育,苹果在孕育。
临街一家商店门口,几盆向日葵高高地举起了命运的圆盘。
逆着阳光,你能看到梵高的纯真,圣火一样的欲望,燃烧吧、颤抖吧!
苏格拉底站在死亡的门前,思考的不是生命的空虚,而是它的重要。
是的,在这单向的生命旅途中,没有什么比生命本真的光芒,更值得骄傲和炫耀。
所以,站在二〇〇三年六月的秦岭路上,我抬头仰望,太阳在天上大笑!
2003年6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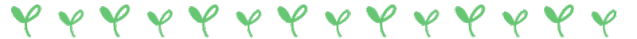
补记:
今年的六月,天空像着了火。人们在抱怨炎热和干旱的时候,谁还会记得去年此时的雨水丰盈呢?
当我们开始憎恶的时候,谁还会记得曾经的爱慕呢?
当我们举杯相庆的时候,谁还会记得那个落寞的背影呢?
当我们开始左右逢源的时候,谁还会记得年少时的梦想呢?
如果你认真地观察过每一个日子,就会发现每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既不普通,也不特别。
天地无私,日与夜,草与木,水与火,爱与恨,一切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物极而反,生动宁静。
只有我们如此善变,在如此强烈的渴望中不停地遗忘。
落笔间,雷声滚滚,大雨倾盆。
2024年6月15日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张新彬
张新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