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秦老师亲自讲述,欢迎收听音频版
秦老师亲自讲述,欢迎收听音频版 】
】
去年此时,上海刚刚“解封”,我去了不少城市调研,既看到“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人人都在熬”,也看到了“用有力代替无力,用有为代替无为,用无畏代替逃避”的抗争。(《拒绝无力》)
今年我在调研中总的感觉是,从上到下,方方面面,付出了比去年更大的努力,但外部性和内源性,周期性和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历史性和新发性,扩张性和约束性,非经济性和经济性,诸多问题综合叠加,压力更大,很多人觉得更难了。风高浪急,惊涛骇浪,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并非遥远的虚词。

何处求解?
不少读者希望通过“大视野”对经济有一些较为客观的认知,我勉力为之,已写到第八年,没有一周中断过。
其实,我自己对经济的运行也常常陷入矛盾。
比如要不要强调GDP。没这个指挥棒,不可能有今日之发展,但代价呢?也很大。我在不止一个地方听到,很头疼的就是上面要数据归真,但究竟挤多少水分,很微妙。如果都挤掉,升迁的前任怎么想?排名掉下来,影响了信心怎么办?真的掉了,上面又会怎么看?以后还给不给你新的机会?
怎么办?听到的答案是:“不挤不行,挤多了也不行,最好一边挤一边加快发展,让发展的盖过挤掉的。发展是硬道理。”
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按传统模式继续发展,还有空间吗?
又如乡村振兴。这些年投入不少,脱贫攻坚成绩显著。但我在一些地方看到的趋势还是城市化,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逢年过节才回来,盖的新房也就在这时住一下,然后一把大锁一锁就是半年一年。有的村子真就只剩下少数人家,怕动物出没,也迁到镇上、县里。
这种情况不独我们有。有学者到日本名古屋市做城市化课题研究,说名古屋市也鼓励下乡,给愿意下乡的市民补贴,甚至白送房子,还给房屋维护费,但几年下来,这些下乡的人又回城了。
有发展商说,他到县城搞开发,首先要开车把县城周围的村镇都看一遍,如果靠近县城的村子盖了不少新房,他才敢投资。因为村里人外出打工,出人头地,首先会在村里盖栋房子。“如果新房都没盖,他是不会到县城买房的。”
看着高速公路两边那些很少住人的新房,我想,中国的城市化,既可以说门槛很低,农民工容易进城,城里也不用给其市民待遇,也可以说代价不低,因为他们辛辛苦苦挣钱盖的房子,就这么空着,从投入产出看,并不经济。
再如,应该投资拉动,还是消费驱动?如果是前者,那就继续走“基建+新基建”的路子,如果是后者,就应更多地补居民端、消费端。我刚去过日本,日本的宏观负债率很高,负债的相当部分用于城乡一体的社保医保,居民安全感很强,就算失业也有保障。
我们的负债主要用于投资,是不是该稍微歇一歇,让灵魂赶得上脚步?有数据显示,到2022年末贵州省的高速公路总里程为8331公里,而日本为7800公里。我们这么严峻的化债压力,还要大力举债大搞基建吗?
各地都困于支出压力,有些支出也令人有些迷茫。我曾听某省一位社科界老领导抱怨,说省里的文化部门排了一出戏,花了3000万,就演了一场。我以为结论是“文化演出也要讲效益,讲市场”,结果他说,我们再排这出戏,也赶不上别省的越剧版那么经典,为什么不换一下我省古代剧作大家的剧目?
我无语。但不敢问“不排行不行”。因为文化很重要,传统文化很重要。我也不敢问“有些预算能不能省”,因为对一个部门来说,今年省了预算,明年上面给的就少了,没有谁愿意在自己任上让预算萎缩。
去年因为疫情,大环境不好,我却找到了不少无所畏惧的正能量。今年继续找,却发现了很多问题,谁都有道理,谁都在努力,国家也付出了很大的人财物力,可问题依旧在,越积越辛苦。
怎么办?这是几个朋友给我的回答。
一位年近七十做民办教育的朋友说:“天塌下来当被子盖,先睡一觉再说。”
一位经济学者说:“越是难,越可能有大的改革。”
一位地方官员说:“历史告诉我,再大的问题,党最终都能找到解决办法。”
挺奇怪的,听他们这么说说,我的心好像真的放下了一些。
也并不是阿Q式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我想的是,既然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不如想一想看问题的态度和角度——如何让问题真实地浮现,如何将问题的来龙去脉真正呈现,然后在建设性互动中进行理性分析,寻找现实的最优解。
老朋友王建宝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长江商学院做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推广。他说,有些问题难解,可能是因为看问题的距离太近,不如离远一点,说不定能有些新解。他邀我参加5月30日在江西上饶市铅(yán)山县举行的“千古一辩”书院文化交流大会。
上饶被誉为“千年读书之地、千古一辩之所”,由宋至清,有过160多所书院。位于铅山的鹅湖寺,是公元1175年理学大师朱熹和心学大家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交流辩论之地。
这场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格物致知”与“发明本心”的辩论,史称“鹅湖之辩”,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我去了铅山,去了鹅湖书院,还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及建宝一起做了对话交流。
鹅湖之辩,余音绕梁。横渠四句,发越千年。追思848年前的理学与心学之辩,赓续斯文,对我是一种精神享受;返本开新,则让我在回归现实问题时,有了一些新的体悟。(注:横渠四句,指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鹅湖之辩
1175年农历六月初三,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吕祖谦(南宋著名理学家)共会于鹅湖山上的鹅湖寺,探讨哲学和治学。此前,朱熹和吕祖谦在福建武夷朱熹的寒泉精舍用了一个半月研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摘取出600多条,编成《近思录》一书,也相当于做了一次备课。陆氏兄弟则在赴约前,预先试辩,直至深夜。
朱熹最强调的概念是“理”。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是“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这都是“形而下之器”,但形而下之器之中,各自有个道理,这就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陆九渊最强调的是心。他主张“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自幼天分奇高,三四岁时就问父亲,天地的尽头在哪里?(“天地和所穷际?”)多年后他读古书时看到“宇宙”二字,“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穿越回到孩童之问,顿悟曰:“宇宙内事,是己份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这场辩论进行了三天。这一年,朱熹46岁,陆九渊37岁,吕祖谦39岁,皆是思想上的黄金时代。
朱熹强调格物致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积月累,穷尽事物之理,“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即多读书,多观察,再分析、综合、归纳,最终把握到那个“先于物而存在”的“理”。
陆氏兄弟的观点则是明心见性。他们说:“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反对在读书穷理上多下功夫,认为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先立乎其大者”,立心最重要,去此心之蔽,即通晓事理。陆九渊还用“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描述双方的不同,批评朱熹的治学方法是“支离事业”,自己的则是“易简工夫”。
这场鹅湖之辩,未分输赢,双方也不欢而散,但并没有自此不相往来。作为中间的调和者,吕祖谦秉持公允,既指出朱熹过于较真,建言他“争较是非,不如敛藏收养”,也批评陆九渊不应针对朱熹本人。
按后人的叙述,这一天,“会者百人。云雾聚,一何盛也。”座中除了学人之外,也有不少官员,如宜春主簿举进士者刘清之、临川太守赵景明、太平州司户进士赵景昭、泉州安溪主簿何叔京、庐陵主簿范念德、德安府司户进士邹斌等。
鹅湖之辩后,朱熹和陆氏兄弟仍各持己见,但彼此尊重,同时也检视了自己的不足,学习对方的长处。朱熹虽然对二陆的言辞滔滔和急迫之势感到不快,但归途中写下《过分水岭有感》一诗,表达了求同存异的精神。“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他后来还反思说,“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太支离处”。
陆九渊也有反思。他一向主张“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但从朱熹身上,他也意识到,“议论时却肯向讲学上理会”。他后来在给吕祖谦的祭文中也写道,“亦自悔鹅湖之集,粗心浮气”。
公元1181年,朱熹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彻夜不眠,充分准备,发表了关于义利之辩的著名演讲。
他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入手,提出区分君子还是小人,主要看志向在哪里。虽然在科举取士制度下,“为士者固不能免此”,但如果只是“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只是为了投有司之所好,则虽然读的是圣贤书,却与圣贤“背而驰”。他说,那种“志之所向”都“惟官资(资历职位)崇卑,禄廪(俸禄)厚薄是计”的人,怎么可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民间疾苦)”呢?只有“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这才是君子所应为,这样做了官,才会“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这样的人,“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在《自作主宰:陆九渊的哲学》一文中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考虑任何问题都是各种要素的权衡、综合,在各种权衡、综合中,对发心动念那一念之微的分辩是至为关键的。做一件事‘最根本目的是什么’,初心是什么,这是君子小子的分野。……人的行为,这一念之差、一念之微是分别善恶的根本:你到底是想成为一个好人,还是想成为一个坏人,你到底是出于利之心,还是出于义之心,你到底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都在这一念之微。这是陆九渊最发人深省、最大震撼人心的地方,这一念之微的分辨是心学得以挺立的根由所在。”
对陆九渊的义利之辨,朱熹深表认同,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他说,“凡我同志”“当共守勿忘”“于此反身而深察之”。他还请陆九渊把讲稿整理出来,并亲自题跋,刻成石碑,即《白鹿洞书堂讲义》,作为书院学子必读之物。
300多年后,陆九渊的心学传至王阳明,经其再发展,成为“陆王心学”。王阳明说:“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王阳明一开始也是对着一棵竹子格物苦修,后来龙场悟道,将理学心学融为“致良知”的“知行合一”之学,“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完成”。在某种意义上,到他这里,“鹅湖之辩”最终画上了一个句号。
鹅湖之辩13年后,一个深雪之冬,两位著名词人,也是抗金将领的辛弃疾和陈亮,来到鹅湖寺。当夜,两人对酒当歌,极论世事,共商复国大计,却又因报国无路而涕泪长流。史称“鹅湖之晤”或“第二次鹅湖之会”。
辛弃疾是我最喜欢的词人之一,他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就是写给陈亮的。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杀敌报国,恢复河山,建立功名,多么壮烈的情怀,只可叹壮志难酬,白发丛生。
辛弃疾在上饶生活过27年,铅山就有一座辛弃疾文化公园。很想去看看,可惜因为修路的原因,没来得及。留下一个念想吧。

从鹅湖想到的文化与思维
今天的鹅湖书院,坐落在国家级森林公园鹅湖山的北麓,一片绿林深处。规模不大,却错落有致,很有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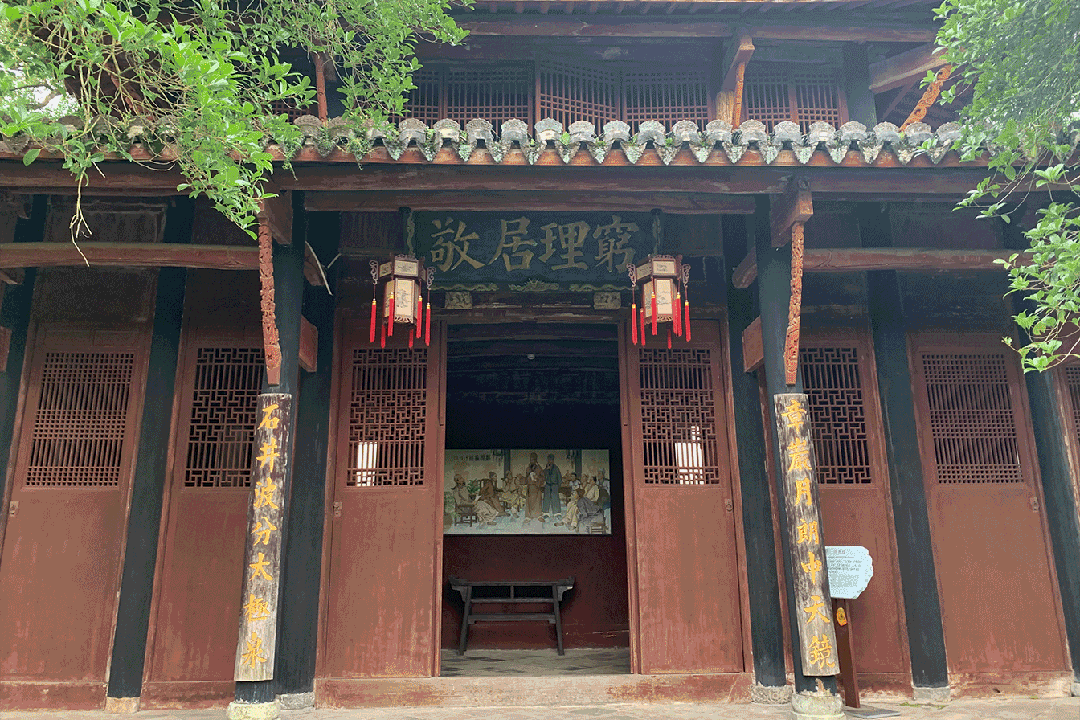
鹅湖之辩发生于鹅湖寺,早已泯灭。公元1250年,宋理宗为山下的一处书院赐名为“文宗书院”,公元1453年,明景泰四年,重修扩建,正式定名为鹅湖书院。1717年,康熙亲书“穷理居敬”匾额赐予书院。目前书院每年接待的客人中,1/6为海外的专家学者及文化团体。
就个人而言,对辩论双方的观点,我更接近朱熹。我赞同吕祖谦的评价,“元晦(朱熹的字)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陆九渊的字)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所谓“欠开阔”,是对陆九渊的认识论有些流于空疏的婉转批评。
但对陆九渊在白鹿洞的演讲,对他不攀权贵,“专志乎义”“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的君子之道,我则敬佩不已。
人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的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活动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在我看来,这种“较高的内心活动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今天之所以荒芜了很多,固然有环境的影响,与我们缺乏超越性的追求也分不开。
钱锺书在《释文盲》中指出,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
于鹅湖书院遥想800多年前的中国学人风采,真真是心向往之。

|铅山葛仙山景区
最后,我把参加“千古一辩”书院文化交流大会的几点思考汇报如下:
1、文化就是交流,交流就是文化。没有交流、交锋、交汇、交融,真知和思想很难涌现。没有往来,没有外来,也不会有未来。
2、交流是平等的对话。有辩,有会(陈来先生就主张“鹅湖之会”的提法),有容,有恕。这才是荀子所倡的“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的君子的辩说。
3、交流需要学习,需要有知识的根底,需要下功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如朱熹所言,“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而为学的第一工夫,就是“要降得浮躁之气定”。
4、文化需要践行。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致知力行,就是要把明的理、穷的理,见诸于行动,“力行其所已知”。
5、士志于道,“专志乎义”。在义利之中要有辨别力,“切己观省”。
当今中国的经济问题,众说纷纭,复杂难辨。唯其如此,找到一种看待问题、反映问题、求解问题的机制,创设一种好的氛围,比具体的一招一式重要的多。
如果能上下交流,内外交流,平等交流,多元交流,用事实、知识和真话交流,用超越性的精神,跨越唯有一己之私的立场去交流,假如有这样的场域,我们一定能找到更好的解题方法和具体路径。
有问题并不可怕。前提是走到解题的正途上。首先,一定不要回避问题,一定要看清楚问题,然后集思广益,众志成城。那些实事求是勇于反映问题的人,那些在诸多约束中仍点点滴滴推动问题解决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所需的朋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朱熹的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辛弃疾的词。
谢谢鹅湖山下的鹅湖书院。在这里,从文化看经济,我有了一些新收获。凭着“记录中国时刻,推动商业文明”的初心,我也会继续在苍茫大地上寻找创造力的活水。


秦朔朋友圈
秦朔,媒体人、原《南风窗》总编辑,《第一财经日报》创办人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