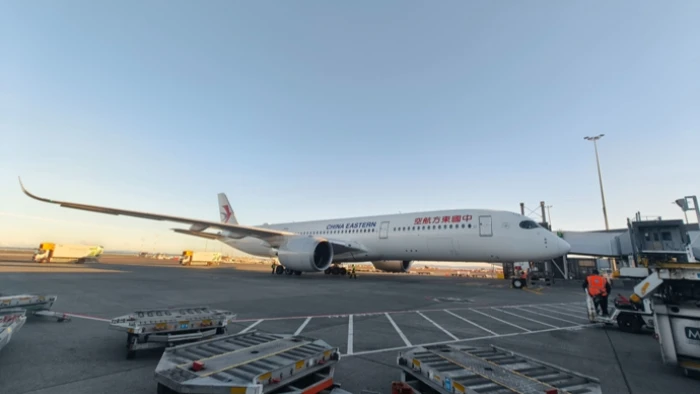“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抄《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这是郑振铎先生在《我的一个要求》中写下的话,批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
在相当时期,林传甲的这本书被视为国人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但据学者陈国球在《文学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中钩沉,当时共有三本书,出版时间接近:
一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字史》,共53页,可能是南洋师范的教材,脱稿于1897年,1906年正式出版。
二是黄人的《中国文学史》,170余万字,1904年开始撰写,1907年作为东吴大学教材内部出版。
三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7万字,1904年印成讲义在京师大学堂内部流通,1910年出版。
三本书中,林著传播最广。这可能是因封面印有“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字样,似乎“高大上”,其实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仅任教一年,当时该学堂还不是大学,此书是“优级师范科”的讲义,林传甲只写了三个多月,未认真对待,但本书也有可取之处。
林传甲生于1877年,福建侯官县(今属闽侯县)人。祖父林宝光曾任成都府通判(正六品),父林文钊在湖北应山县当过典史(未入流,九品之下)。林传甲6岁丧父,母刘盛出身名门,在她教导下,林传甲于1902年中举,但次年会试失败。1904年,经同乡严复推荐,28岁的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任教。
林姓是福建巨族,林传甲曾说:“每遇改革之际,吾闽林氏必牺牲一二同胞以为纪念。戊戌变法时之林旭,黄花岗之林广尘(即林觉民),首入南京之林述庆(辛亥福建三烈士之一),皆最著者也。”
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中,能看出他也是个敢离经叛道的人,比如他写道:“吾读诸子之文,必辩其学术,不问其合于儒家不合于儒家,惟求其可以致用者读之。”“吾惟视今日之实学,远胜古人,不欲使才智之士,与古人争胜于文艺,明白晓畅,尽人可知,何必为古人之奴隶乎?”
今人读这本书,难免大吃一惊——竟从文字变迁讲起,接着是音韵变迁、训诂变迁、古今文章之别,直到第八篇(全书共十六篇),才开讲周秦传记杂史文体,总算有了一点文学史意味,如此编目,系直抄当时的教学大纲,可见本书“非专家书而教科书”。
细读下去,更觉离奇:本书只讲散文史,不及其他。林传甲对日本学者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将杂剧、院本、传奇、小说等也视为文学,深感不满,甚至说:“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
林传甲观念落后,不懂文学史,但他的主张中,有重实学的原因。当时科举未废,学生仍需“练习各体文章”,而大量灌输文学知识,只能给学生以“表面博学”的幻觉,无法真正提高写作水平。
清末人眼中的文学,专指操练各种实用文体的学问,在《中国文学史》中,论述了如何写应用文、公文、告示等,林传甲认为:“今日撰中国历史者,溪径各别。虽周秦古事,亦注意今日政策者,然后知修史之材与作史之法,皆归于致用也。”而今人眼中的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与实际应用无关。
林传甲的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有志从政,愿通过文字思考、自我修炼的读者。直到清末,他们还是主流,世易时移,如今已被边缘化,难得后人理解。
1905年,林传甲去广西当知县,不久又去了黑龙江,成为当地教育变革的先锋,并作为教育学者、舆地学者而青史留名。
学者陈国球认为:“《中国文学史》并不是林传甲的重要著作。”“至于他留下的‘讲义’为后来的文学史论述带来了什么深义,相信他本人不会非常在意。”不过,抛开今人对“文学史”的定义,品味林传甲所理解的“文学史”,亦别有一番滋味。
1922年,林传甲因病逝世,年仅45岁。他一生著述甚勤,弟子众多,他后在中学又讲授过“文学史”,不知是否仍用这本讲义。
本书1904年版、1906年版已佚,现存最早的版本应是1910年武汉谋新室版。想真切感受古代“文学之士”的状态,本书仍可作门径。
(作者 唐山 来源 北京青年报)
统筹:梁冰
编辑:许怡童


 iPhone版
iPhone版  Android版
Android版